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我喜欢海岸线、锋面以及国界,因为在这些地方总能看到耐人寻味的摩擦与矛盾。
这句话来自非虚构著作《要命还是要灵魂》的序言,同时也概括了全书的主旨,即如何理解那些无可避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化冲突。
位于冲突与风暴中心的是一名叫做李黎亚的苗族女孩,她居住在美国默塞德县,活泼任性,脸蛋圆圆,惹人疼爱。20世纪80年代,她被诊断为严重癫痫症,县立医院出动了最优秀的医生进行救治,黎亚的父母纳高与弗雅也为其倾尽心血。但黎亚还是一天天衰弱下去,最终成为植物人,在30岁时与世长辞。
在黎亚的故事里,一部分是医患双方绝望的争执,医生头痛于苗人不遵医嘱也不讲英语,本就不畏强权的苗族人则对医学权威嗤之以鼻。黎亚的父母相信,孩子得病是因为灵魂被恶鬼掠走,这也是《要命还是要灵魂》英文书名的由来——“当恶灵抓住你,你就跌倒了。(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苗人信奉万物一体的泛灵论,医疗就是宗教,宗教就是社会,“当患有疾病,斩断鸡首便可治愈。”但西方的医疗文化和医疗分工并不这样认为。
另一部分的黎亚故事与历史和根深蒂固的民族创痛相关。美国曾在越战的老挝战场上秘密训练苗族部队,战争使得大批难民流离失所而被迫来到美国,黎亚的家人便是其中一员。寄人篱下的苗人不仅要经受战后的身体疾病(因此成为医院常客),还要面对普遍的高度焦虑与抑郁。黎亚的母亲就总是陷入自卑情绪,她曾以高超的刺绣技艺为荣,却无法在美国施展拳脚。女儿患病后,她甚至连做母亲的能力也遭到否认——由于不按要求给女儿服药,法院宣告弗雅虐待儿童。正如另一名在圣地亚哥遭受人身损伤却不愿自卫的苗人所说,与故乡相比,“这里没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挺身而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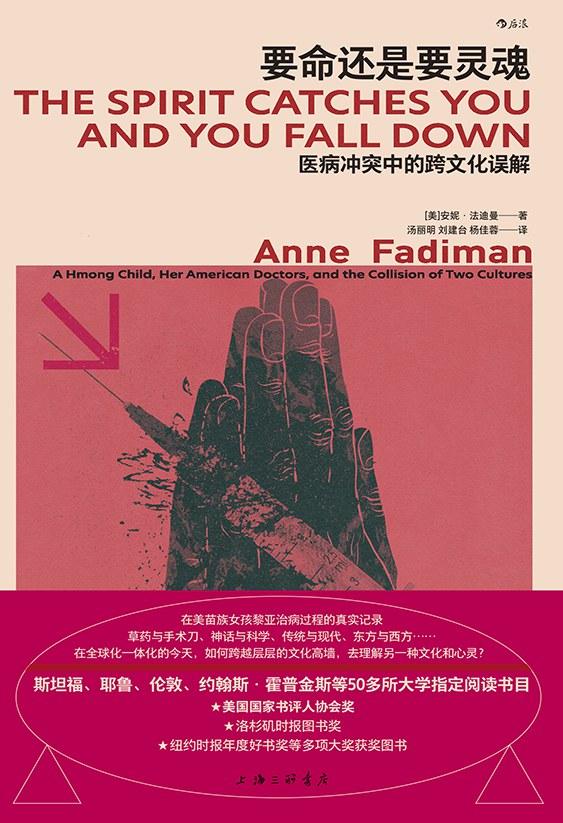
[美] 安妮·法迪曼 著 汤丽明 刘建台 杨佳蓉 译
上海三联书店·后浪文学 2023-2
上世纪80年代末,来自纽约文学世家的安妮·法迪曼“抓住了”这个故事,故事也抓住了读者。《要命还是要灵魂》初版于1997年出版,跻身年度畅销书榜,同时也成为了包括耶鲁医学院在内的高校必读经典书目。
它的出版恰好呼应了美国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模式的兴起。在近年的医学人类学界,关怀伦理(care ethic)正在进入民族志学者的视野。在此背景下,《要命还是要灵魂》甚至成为了医学人文学科的一种语境,提出了许多紧迫的问题:我们能拥抱更多元的医疗模式吗?盛行成功叙事的西医模式要如何面对致命的医疗过失?真正以人为本的照护又是怎样的?时隔近三十年,面对一个族群分裂日益严重的世界,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在本书于中文世界出版之际,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专访了安妮·法迪曼,希望与她重返黎亚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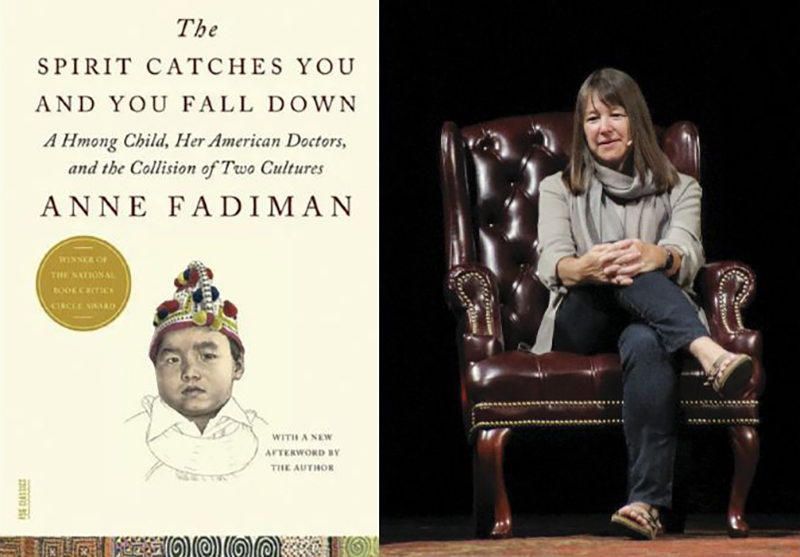
01 小病号连接着整个宇宙
界面文化:越南战争后,苗族难民分散于美国大陆,但许多美国人并不了解苗人在老挝战争中为美国效力的情况,也不了解这个民族。你当时为什么会对在美苗族产生兴趣?
安妮·法迪曼:我之所以会对苗族感兴趣,是因为我的一位老朋友——他也是我哥哥大一新生时的室友——是加州默塞德县医院的住院医师。在互联网兴起之前的那些日子,我们每隔几个月就通一次电话(那可是在1988年),在一次谈话中,他提到医院里突然涌现出许多苗族病人,他们都是来自老挝的难民,医院的同事们觉得他们充满魅力,但也非常令人沮丧,因为他们拒绝接受标准的西医治疗。
我之前听说过苗族人,但对他们知之甚少,所以我想去探访默塞德,试图找到这样一个案例:它的失败并非出于个人的恶意,而是由于文化间沟通的不顺畅。
界面文化:这本书采用了双线叙事的方法,它不仅是黎亚的故事,也是苗族人惨痛的战乱和流散的历史。你曾在2001年的演讲中说,黎亚这个小病号像是一根线,而最后这根线连着整个宇宙。能谈谈你是如何发展出这个“宇宙”的吗?黎亚与苗族难民在美国境遇的关系是怎样的?
安妮·法迪曼:书中的叙事方法并不是我发展来的,纯粹是现实给予我的。刚开始,我以为我只会发现一个医疗案例——关于一个孩子、她的父母和她的医生,结果却发现它和更大的问题相连,比如战争、家庭、文化、人们如何沟通、怎样才是好的医生、怎样才是好的父母。
黎亚出生在美国,但是她的父母和大多数兄弟姐妹都出生在老挝。由于《日内瓦协议》禁止美国向老挝派遣自己的士兵,所以在越南的老挝战场上,美国雇佣了许多苗族人为自己作战,他们的工资远低于美国士兵,伤亡率却远高于美国士兵,我认为这是我的祖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事件之一。1975年,巴特寮(即老挝爱国战线)和北越南夺取了老挝政权,由于苗族人此前帮助过美国,他们便成为了被新政权戕害的对象,于是只能被迫离开老挝,这15万难民里就包括黎亚一家。

界面文化:2012年是这本书出版的15周年,黎亚也是在这一年去世的。你在成书之后有再去探望他们吗?你如何评价黎亚的一生?我在想,虽然黎亚是文化冲突的受害者,但她也得到了来自家人和医生的宠爱,就像一名遇难的公主。
安妮·法迪曼:黎亚于2012年去世,大家都很伤心。我去了她的葬礼,也和她的家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今年夏天,黎亚的九位家人要来我在马萨诸塞州的家中做客。
黎亚患有癫痫病,即使家人按照处方给她服用药物,也很难完全治愈,何况他们出于各种原因没有这样做。为了确保正确给药,黎亚被送到一个白人寄养家庭生活了大约一年,才被送回父母身边。黎亚的一生是悲惨的,她慈爱的父母和受过教育、用心良苦的医生都希望对她好,却都无法理解对方,个中原因实在很难付诸于语言。

02 文化冲突与在美苗人
界面文化:黎亚的父母是战后第一代美国苗族移民,他们被迫来到这里,不愿意融入美国。近来在美苗族群体的生存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观,这一代人也对美国文化更为认同了。但是另一方面,今天亚洲族群在美国被歧视的情况仍很常见。苗族人对这些变化有什么反应?如果这本书写在今天,可能会有什么不同?
安妮·法迪曼:正如你所说,虽然许多文化传统得到了保留,但在美苗人已经很大程度上被美国文化同化了,尤其是50岁以下的人,他们很有可能接受的是美国教育系统的教育。当然同时也存在大量针对亚裔的歧视,情况比我写书时要复杂得多,苗人的宗教、政治所属、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都各自不同,再也无法被简单地概括。
我没法回答我会怎样重写这本书,因为如果是在今天,我根本不会写它。当我在80年代末做调查时,我能读到市面上所有关于苗族的英文和法文著作,这也是我唯二懂得的语言,但是如今相关的文献资料太多,光是阅读就要花几辈子时间。而且,虽然我深信人们完全可以写自身文化之外的东西,但是现在有许多优秀的苗族作家在用英语写作,在2023年写黎亚的故事更像是一种挪用的行为,不再是出于尊重的行为。
界面文化: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本书中的苗族文化有些静止不变,你如何看待这种批评?
安妮·法迪曼:这是一个公允的评价,前提是人们理解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而我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进行的报道。当时几乎所有苗族难民抵达美国时都有差不多的背景,所以可以用“苗族是……”、“苗族人相信……”这样的句式。但是今天我肯定不会这样说了。不过,我希望我的书仍有一定价值,可以作为美国难民史上一个特定时期的缩影,也可以让人们思考跨文化医疗的一些核心问题。

界面文化:这本书也成为一本旨在培养“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y)的教科书,但是正如你在书中提到的,这个词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为什么这个概念值得批评?
安妮·法迪曼:“文化能力”意味着医生应该去学习、掌握的某种技能,这个词在1990年代很受欢迎,但是它也受到了公允的批评,因为没人能真正完全“掌握”别人的文化。我最近经常听到的另一个词是“文化谦逊”(cultural humility),它承认医生对病人的文化有许多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的地方,并且医生这边的文化也不一定是最优越的。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使用了医学人类学者凯博文设计的病患问题表,旨在了解和关怀病患自己的想法。凯博文在著作《照护》中提到,他所重视的照护理念受到中国古典文化影响。书中苗族的传统治疗也相当注重对病人的照料和关怀,而不只是攻克疾病。在你看来,苗族的巫医医疗可以提供怎样的启发?你又如何看待非西方的世界观?
安妮·法迪曼:如果我的家人生病,我不会去找苗族端公(即巫师),而是找在美国医学院受过培训的医生。事实上,我的女儿就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换句话说,我们对现代生物医学抱有信心,但它也肯定有局限性。
苗族端公到黎亚家进行治疗仪式时,会提供很多医生无法给予的东西,比如他很了解这个家庭,他关心患者作为人的境况,他讲他们的语言,会登门拜访,和他们共处好几个小时。虽然西医暂时无法上门服务,但我认为他们应该对病患表现出更多同理心和人性关怀。
我更愿意把科学与非科学的世界观看作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二者的关系是“既是/又是”,而不是非此即彼。我自己并不认同非科学的世界观,但我知道在一个越来越非人性和技术化的世界里,它们拥有珍贵的吸引力和价值。

界面文化:你在书的后记中提到,现如今苗族的祭祀活动已经融入了默塞德医疗中心和其他组织。根据你的观察,它是如何实施的?还存在哪些问题?
安妮·法迪曼:默塞德的县医院现在允许苗族巫师探望病人,在床边做治疗仪式。虽然我个人不相信这些治疗仪式的精神性基础,但我百分之百相信它们的价值。这些仪式十分强大,可以在紧张的医院环境中给病人或家属的心理健康带来巨大改观。
其余问题主要与以下事实有关:一些在美苗族人仍然对西方医疗的某些方面有抵触情绪。另外,尽管年轻的苗族人能说流利的英语,但年长的苗族人还是需要医院的翻译服务,翻译质量参差不齐。
03 召唤灵魂,回到故乡
界面文化:你曾在采访中称自己不是一个“客观的记者”,不过你在展现美国医生与苗族人的时候,尽量对双方带有善意和理解。你是怎样把握真实与个人表达之间的平衡的呢?
安妮·法迪曼:某些类型的新闻报道,如头版新闻报道,绝对应该是客观的,记者的个人观点不应该掺杂其中。但是,由于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世界因你所处的位置不同而显得不同”,所以我试图做到准确和公平,不过我从未试图“客观”,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当我写到黎亚的母亲时,我怎么可能客观呢?她曾把我打扮成苗族新娘,好说服我的男朋友向我求婚。
我不觉得真实性和自我表达有冲突。我试图使这本书尽可能准确,比如我请医生对医学方面的段落进行了审核;一位越南战争的历史学家检查了关于苗族在老挝秘密战争中的作用的章节。在我写到自己的感受或经历时,我也尽量做到真实。
界面文化:全书的最后一段令人印象深刻,它是一段不断重复的咒语,似乎既是对黎亚灵魂的召唤,也是对苗族人回家的呼唤。这个诗意的结尾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又如何理解民族志或非虚构写作中的文学性?
安妮·法迪曼:这本书的结尾是一位“灵魂召唤者”在李家协助端公进行治疗仪式的场面,他站在公寓门口对着黎亚的灵魂吟唱,请求它回来。咒语的最后一句话是“回家吧”,一共重复了七次。
在三十多年前的在美苗人中间,传统的苗族信仰非常普遍,它认为许多疾病是由于灵魂丢失造成的,灵魂归来也就意味着康复。对我来说,“回家吧”这句话似乎特别悲伤,虽然召魂者不一定想到了老挝,但我在仪式的当下立刻意识到,黎亚的父母和其他苗人仍然视老挝为他们的家乡,他们很想回去,但那是不可能的。值得一提的是,黎亚的兄弟姐妹都成为了成功的美国人,其中许多是大学毕业生,从事着各种职业,他们视美国为家,也不再希望离开了。
我的确喜欢在写作中加入作家个人的声音和观念,还有独特的幽默感和悲剧感,但是召魂者的咒语没有让我觉得特别“文学”,我只不过是很幸运地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那里,用录音机录下了他的原话。
最后我想说,在写整本书的过程中我都很幸运。《要命还是要灵魂》事关两种文化:苗族文化与美国医疗文化,我笔下的家庭与医生都是我喜爱和尊重的人,他们愿意让我花大量时间询问那些痛苦的经历——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对于黎亚一家,这些经历对于医生来说也同样痛苦。如果没有他们的慷慨相助,就不会有这本书。我在美国医学院向读过这本书的学生演讲时告诉他们:书中的教训并不属于我,它属于黎亚,我只是遇到了这个孩子,花了几年时间思考她身上发生的事情,并把我学到的东西传递下去,归根结底,我只是一名传达者。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