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福克斯出生于伯克郡的纽伯里,今年65岁,因设定在法国的历史小说《狮子的女孩》(The Girl at the Lion d'Or)、《鸟鸣》、《夏洛特·格雷》(Charlotte Gray)而出名。他的新书《巴黎回响》(Paris Echo)从一位美国博士后研究者和一位摩洛哥年轻人的角度分别进行叙述。
《卫报》:你的小说从外国人的视角描绘了巴黎的图景,你在巴黎待了多久?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我17岁时第一次去巴黎,住了三个月。我当时和一位老太太住在大军团大街,就在香榭丽舍大道下面。那是孤独但又充实的一段时间,我读了很多书,下午去逛画廊或者看电影。我爱巴黎,但我当时年纪太轻,又没钱,无法融入主流艺术圈。那时候还得会说法语才能融入当地社会,现在就不一样了,餐厅的服务员很乐意练习他们的英语口语。当我决定要写一本以巴黎为背景的小说时,我去巴黎住了两个月,2016年的二月和三月。我在第九区的弥尔顿街租了一间公寓,就在皮加勒区南边,是典型的50年代风情法国街区,而不是中国人或意大利人聚居区。那时巴黎刚刚经历《查理周刊》总部枪击案,整个城市弥漫着灾难后的情绪,但我仍然觉得巴黎是个生动的城市。
《卫报》:你喜欢法国吗?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当然了,按照顺序,我喜欢这里的风景、艺术品、红酒,然后是美食和文学。90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妻子维罗妮卡在法国西南部的阿让市(Agen)附近住了一年,忍住了没买房。我们要维护伦敦房子的开销就已经够艰难了。
《卫报》:这部小说描绘了“另一个自我”和“灵魂出窍”的故事,你是怎么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的?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每周,我在法国文化协会上两次夜课,提高我的法语阅读能力。和大多数英国人不一样,我的法语口语很不错,但却无法完全理解法语的文字内涵。老师给我们讲了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和“自窥症”。我开始对此着迷。在《巴黎回响》的开篇,我引用了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著名诗句:“热闹的城市充满各种梦想/白日的灵魂与路人对质!”17岁的时候我在巴黎度过了充实的时光,后来我重新回去,在地铁上见到的大多数女性都和我当年触不可及的女性没什么区别。在地铁上,每个人的身份都会停滞。这些女神们也会坐在办公室里做无聊的工作,那时可能就不会那么女神了。
《卫报》:每个人都有另一个自我吗?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不一定是字面上的意思。有时候我会想我自己也有很多面,可能会在生活中某个特定的时候做出不同的选择。年纪越大越容易想这种事。历史也是一样,如果拿破仑没有进攻普鲁士,那历史也会有所不同,而很可能只是拿破仑那天早晨头疼一时兴起发起的战争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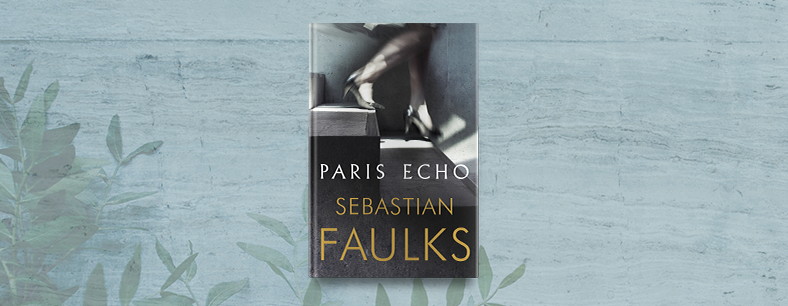
《卫报》:现在和17岁相比,你的性格有变化吗?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我觉得没有。有些性格特点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尤其是在30岁的时候。但我总觉得自己变得不一样了。小时候,我非常非常害羞又紧张,现在不会了。感觉在45岁以前,我已经用光了这一辈子的紧张和焦虑。我的孩子们总是嘲笑我,每当他们问我要去度假是否激动时,我都会说:“我不知道激动是什么了。”
《卫报》:那你的作家身份是否也有很大变化?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现在读者有更大的空间和选择余地,我也没有那么傲慢。我以前写作总想告诉读者:这是你无法理解的事情,之前没有人解释过,但它其实是这样的,你必须要明白。我其实更擅长对话,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对话的意义:是用一种不同的形式给读者提供信息,让他们在大段文字中得到放松。我之前以为对话是用来模仿人们对话的方式。
《卫报》:这本小说也让我们质疑应该如何理解历史,对一段历史的不了解会让人盲目吗?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如果你知道你周围的人、你所在的城市和你自己的历史,才能更懂得生活。这是需要用一辈子去消化的旅程。许多人到了中年才对他们的家族历史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出身幸福家庭的人。我的兴趣是,我这一代人是怎样融入欧洲历史的,我的许多作品都试图解开这个谜团。
《卫报》:在这本小说里,你涉及到了一个很少在小说中出现的主题:法国在驱逐犹太人中扮演的角色。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犹太人从巴黎北部郊区的德朗西集中营被送到奥斯维辛。德朗西原来由法国控制,但法德两国在大屠杀中的合作50年来都没有得到官方承认。年轻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尽管法国合作遣散了8万犹太人,但与其他合作过相比,这一数字并不算高。官方说自己早已承认这种做法:塞纳河岸有一尊铜像,德朗西有一座小纪念博物馆,前总统雅克·希拉克也为法国的同谋公开道歉,公众还需要什么呢?这是看待此问题的一个方式,另一个方式是要问:为什么道歉这么难?作为一个国家,如果50年前就承认此事,国家是否会更安定?
《卫报》:你有多爱国呢?我喜欢你在小说中对英国爱国主义和法国爱国主义的区分。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爱国的。这是个非常英国的说法,对吧?我疯狂地为英格兰足球队加油,但我却对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欧洲议会议员)不满。我为英国在艺术、科学和研究上的成就感到自豪,但认为英国社会仍然有一种不会在法国出现的细微保守主义。法国精英们总认为法国有着教育全世界的任务,但英国知识分子阶层就不会这么想。我不是在嘲笑法国,但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显著差别。

[英]塞巴斯蒂安·福克斯 著 郑冉然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1
《卫报》:如果你可以重新选择国籍,你会选择哪个国家?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我能想出来很多我不想要的国籍。如果住在澳大利亚,又总会想去欧洲。我很想成为法国人,但一定会想念法国作为邻国的感觉。作为英国人的好处就是,18英里外有法国这个非常不同的邻国。但我觉得法国人可能不会有同样的想法。
《卫报》:不写作的时候,你如何放松?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我每周打两次网球。我还参加了“作家十一人队”,我们一起玩板球,已经是乡村俱乐部里不错的水平了。我的孩子们已经分别27、25、21岁了。我的大儿子是足球记者,住在马德里。我女儿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小儿子在曼彻斯特学习哲学。
《卫报》:你的床头读物有哪些?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罗曼·加里(Romain Gary)的小说《风筝》和盖瑞·雪菲尔(Gary Sheffield)记述一战历史的《遗忘的胜利》(Forgotten Victory)。
《卫报》:小说家会有退休的一天吗?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有60多岁的作家很直接地告诉我,他们写作只是为了赚钱,早已没有了真正的写作热情和欲望。但我觉得我还有潜力可以挖掘。
《卫报》:就像地铁上的女孩子吗?
塞巴斯蒂安·福克斯:只要一直生活就能学习很多新东西。我有野心继续写得更多更好。
(翻译:李思璟)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