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Netflix纪录片《美国工厂》正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热议。
这是因为片中描述的“美国工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由美国人建设、管理的工厂,而是一座由中国人投资并全面贯彻中国人意志的“美国工厂”。这座工厂位于美国“铁锈地带”的核心——俄亥俄州代顿市。2008年,通用汽车工厂宣布破产,2000多名员工瞬间失业,令该地区的失业率再创新高。2014年,来自中国的福耀玻璃集团收购了通用留下的旧工厂,雇佣了大量当年失业的蓝领工人。福耀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出口量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创始人曹德旺有着“玻璃大王”的称号。
福耀的到来为死气沉沉的代顿市带来了希望。长期待业在家的工人们无一不欢欣鼓舞,对新工作和新生活充满期待。然而最初的蜜月期很快过去,美国人很快发现,虽然工厂的全称被冠上了“美国”的定语,但福耀并不打算在工厂运营和人力资源管理上走美国的路子。增加工时和提高效率被视为重中之重,为了保障企业的利益,曹德旺直接撂下狠话——如果厂内成立工会,工厂就不开了。
为了向中国学习提高效率的经验,几位美国中层管理人员前往福耀总部。他们震惊地发现,中国工人的工资比美国工人低得多,工作时间也长得多,而且缺乏生产安全装备,但他们安静顺从、一丝不苟,效率高得如机器人一般。回到美国后,他们希望效仿中国工厂的一些做法,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在出现安全事故后,部分美国工人开始抗议示威,要求建立更完备的防护措施并建立工会。在管理层的强硬介入、软硬兼施之下,“反对工会”派在是否建立工会的民主投票中获得了约60%的选票,福耀大获全胜。2018年起,福耀美国开始盈利。

投票结果公布后,中国人奔走相庆,而一位曾在通用汽车工厂工作多年的美国工人感叹道:“通用给了我很好的生活,他们走时,这一切都断了。我们再也赚不到那种钱了。那些日子结束了。”

目前已有1.8万人在豆瓣网为《美国工厂》打出了8.5的高分。有一种声音认为,《美国工厂》反映的是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中国人分分钟教美国人做人”。然而我们真的能嘲笑美国人眼高手低、懒惰难管吗?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和全球经济深刻交织在一起,资本顺着“节省劳动力”的方向进行全球流动,这是美国制造业衰落、中产式微的真相。我们终将意识到,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造就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巨大探底竞争,在劳资关系日益倾斜的天平下,不掌握资本的人终将沦为“进步”的代价,无论身处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是车间工人还是办公室白领。
美国梦碎:“新经济”的出现与中产阶级的式微
“你永远不会放弃美国梦。对我来说,那就太没有美国范儿了。我能有白色篱笆,我能有漂亮房子,如果孩子愿意就送他们上大学,被人以基本的礼仪相待,你必须能够相信这些。” ——《美国工厂》
在大萧条时期,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创造了“美国梦”一词,推动“美国社会里阶级出身并非命中注定,所有人都能凭借努力向上流动”的观念。至今为止,“美国梦”包含着一系列被美国人视为“不证自明”的预想:财物安全、拥有住房、美满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下一代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幸福感、成功的职业、稳定安逸的退休生活。
在这个概念刚被提出的1930年代,“美国梦”与其说是社会现实不如说是一种鼓舞穷苦美国人士气的愿景——当时的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如同金字塔,阶级流动的自由度极其有限,大多数人处于社会底层。美国梦化作现实、成为“真理”要等到二战后。以马歇尔计划为核心的全新地缘政治体系令美国得以通过控制全球3/4的投资资本和2/3的工业产能主导全球经济,保证了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
在那几十年的时间里,工人和管理层形成了“社会契约”式的劳资关系:管理层为工人提供稳定增长的工资、养老金、健康保险和带薪假期;工人(其中很多是强大工会的成员)以高生产率为回报,商定了工作规则并减少未经授权的罢工对工作场所的干扰。美国社会学家厄尔·怀松(Earl Wysong)、罗伯特·佩卢奇(Robert Perruci)和大卫·赖特(David Wright)在《新阶级社会》一书中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后经济重塑了美国的阶级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变为了钻石型。80%美国人进入中产群体的事实说明了阶级流动机会大大增加,美国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即使是蓝领工人,也能自豪地称自己为中产的一员。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梦”成为了美国人牢不可破的信仰。美国作家J.D.万斯(J.D. Vance)在非虚构作品《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写道,不同于今日,1950年代的俄亥俄州曾是大型制造企业云集、工作机会多多的黄金地,吸引着他外祖父母从更贫瘠的肯塔基州来此定居,这里为他们提供了体面稳定的生活,令他们在种种困难面前依然坚持对美国梦的信念。万斯写道,“阿嬷和阿公对于勤奋工作和美国梦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他们也从未幻想过财富和特权在美国并不重要……不过,阿嬷和阿公相信,努力工作更为重要。”

[美]J.D. 万斯 著 刘晓同、庄逸抒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4月
然而事情到1970年代出现了变化。在战争余烬中站起来的欧洲和亚洲重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1977年,美国进出口商品逆差创下292亿美元的新纪录,标志着美国开始从一个债权国变成一个债务国。与此同时,很多美国大公司开始利润下滑。为了应对这一变化,“新经济”从1970年代开始出现。和“旧经济”强调劳资共赢相比,“新经济”更强调节省劳动力,美国公司开始扩大对外投资、兼并、与外国公司联营,并通过关闭工厂和裁减国内劳动力实现外包和离岸生产更廉价的产品。
美国国内经济开始与全球经济深刻绑定,促进这一变化的,是一套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该理念的核心是,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能够为所有人提供最有效经济生产和带来繁荣的唯一制度。虽然短期来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可能会导致失业和工作环境变差,但从长远来看,它能保证所有人的自由和繁荣。
在这一背景下,俄亥俄州这样的制造业重地开始遭受严重打击。二战后一度占美国就业岗位比重达40%的制造业,在1981年滑落至27%,在2010年降至8.1%。从1979年到2012年,美国失去了800万个制造业岗位。2007-2011年,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启动大裁员,其中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从2007年的7.8万人降至2011年的5万人。《美国工厂》的片头所描述的,正是其中一部分失业工人的窘境——成千上万的个体、家庭和社区倒在了裁员的镰刀之下,生活的希望亦被剥夺。
这一大趋势亦对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产生了极大冲击。《新阶级社会》指出,当下的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再度发生变化,从钻石型结构转变为双钻石型结构,“双钻石”指的是代表特权阶级(20%的人口)的顶部小钻石和代表新工人阶级(80%的人口)的底部大钻石。顶层和底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且向上流动的机会非常稀少。占据资本的特权阶级在全球经济扩张中攫取了绝大部分的利益,牺牲的却是工人的利益:
“随着大部分美国制造业基地转移到低薪国家的工厂,公司利润和股东分红在过去的几年中显著增长。同时,剩下的美国制造业工厂中工人工资的停滞或削减以及生产流程的提速,又进一步提升了利润和分红。国外工人的低工资加上削减国内工人的工资和提高生产效率,导致(工厂)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了更多的产品和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在这样的全球生产体系下,哪家公司不能产生更高的利润呢?那么,不断增加的利润又是如何分配的?答案是没有工人的份儿。他们的收入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公司的利润大多以更高的薪水、奖金和其他福利形式分给了高管、管理者和专业人员。”
三位作者认为,抛弃“社会契约”的新经济格局将美国特权阶级和新工人阶级放在了利益对立面,“任何使工人阶级的资源更加稳定的行动(如通过加强工作保障或增加工资和养老金等)将导致特权阶级损失一些资本和利益。”这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式微——中产阶级存在的前提是稳定的工作和安全的金融资源,然而在上述情况下,这些前提正在消失。

[美]厄尔·怀松、罗伯特·佩卢奇、大卫·赖特 著 张海东等 译
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7月
谁的胜利:“无国无家”跨国公司与失衡的劳资关系
“我们60%啊,那我们就太牛逼啦!”——《美国工厂》
在纪录片中,一位密切关注工会投票结果的中国员工在接到同事电话、得知“反对工会”的选票占多数时,这样兴奋地叫道。这一幕构成了一个绝妙的隐喻——应该说福耀美国工厂的存在本身就是这样一个隐喻——在资本和观念之争中,美国正落入下风,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赢家。然而我们真的可以如此乐观吗?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认为,经济关系的地理重组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劳动制度、资本和政体的不断重组,“随着资本家寻找越来越便宜的劳动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大的市场,他们以越来越新的方式结合和重组世界上的工人和消费者、世界上的土地和原材料。”贝克特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集体行动(或缺乏集体行动)以及国家的政策(或缺乏政策)都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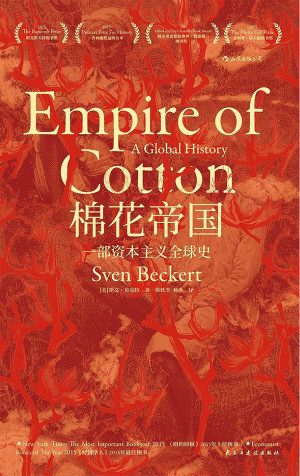
[美]斯文·贝克特 著 徐轶杰、杨燕 译
后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年3月
纵观资本主义的历史,资本家曾与强大国家深刻绑定,共同扩展市场,获取劳动力。然而如今我们看到,资本日益从特定民族国家的绑定关系中解放出来。许多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最新阶段的标志就是无国无家(stateless and homeless)跨国公司的崛起——它们既没有与任何国家政府结盟,也不对任何地区、社区和人民承担长期义务。加拿大记者、社会活动家娜欧米·克莱恩(Naomi Klein)曾在《NO LOGO》一书中指出,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跨国公司纷纷致力于重塑自身业务,将重点从生产产品转向了品牌塑造。企业管理者们开始认为,将有限资源花在终将老损的工厂和员工身上是不划算的,应该将资源集中在品牌营销上。
在这一逻辑下,资本重新分配的速度大大加快了。跨国公司不断将生产从一个低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更低薪的国家,以获取更勤奋更廉价的工人,形成了一场永无止尽的探底竞争。跨国公司甚至不需要自己在海外建厂,只需将生产任务交给承包商就行了;订单下给某个承包商,后者可能会将订单再转包给其他厂商;在某些情况下,订单或许将层层转包最终抵达某个家庭作坊。那些实际参与产品生产的人境遇如何,就和跨国公司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了,因为他们并不是雇佣员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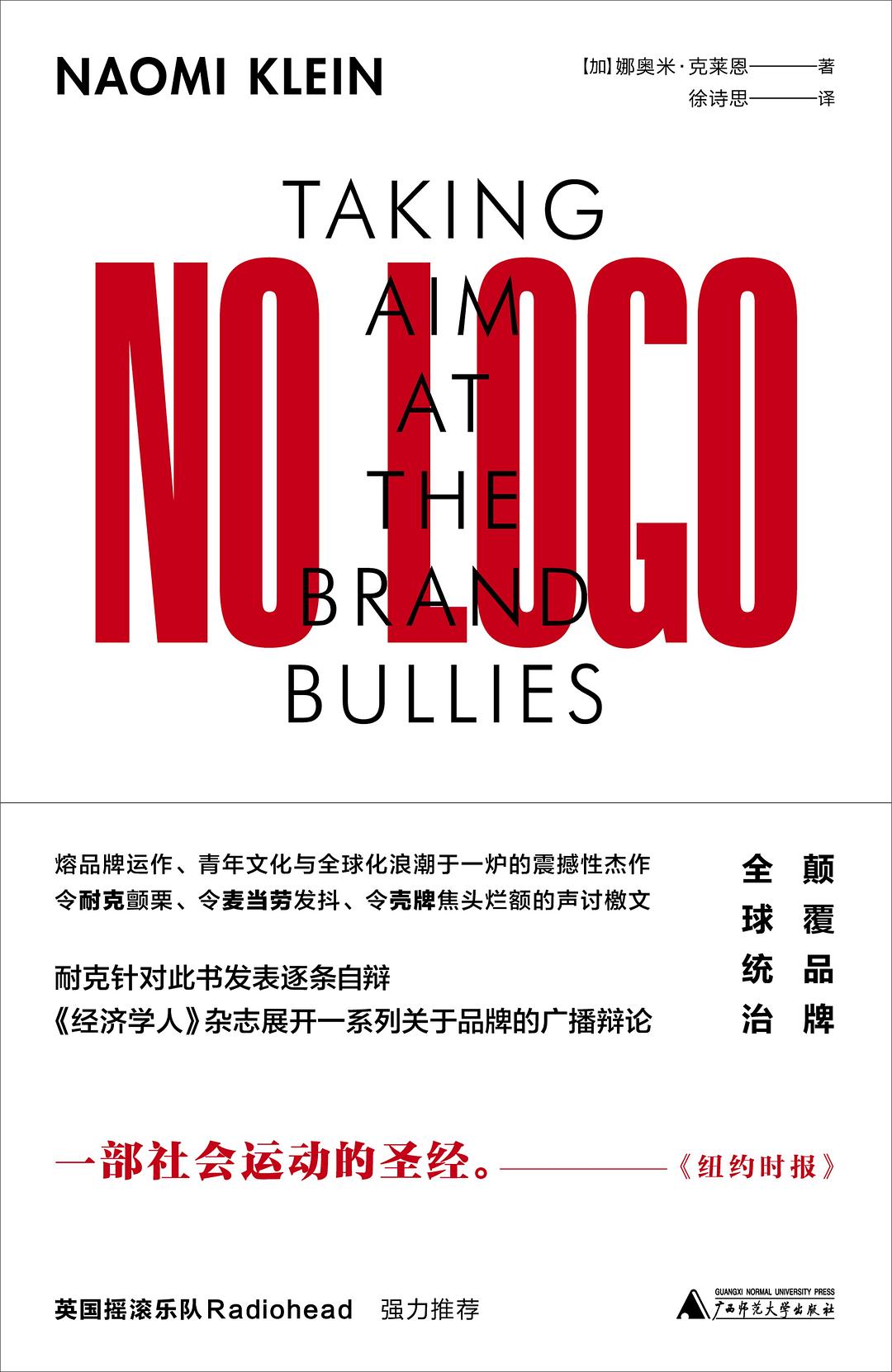
[加]娜奥米·克莱恩 著 徐诗思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克莱恩认为,在这一转包机制的加持下,跨国公司已退回到19世纪的剥削水平:每个环节的制造业者相互竞价,把价格压到最低,然后再抽取利润,最末端的工人于是只能拿到层层盘扣后的微薄薪水。在这个过程中,贫穷国家的工人固然获得了以前不曾有的工作机会,但他们的获益也远没有官方宣传的那么多。克莱恩在实地考察了菲律宾甲米地出口加工区后发现,那里几乎可以说是跨国公司的“法外之地”:为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厂竞争,工人薪资被压到了堪堪温饱的水平,工作时间过长,福利保障几乎没有;政府则因为害怕外商撤资,而不愿干涉加工区内违反劳动法的行为。
在强大的跨国公司面前,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立场很难强硬起来,因为“节省劳动力”的铁律一直强有力地指导着资本的流动方向。“由于产业对上涨的工资、环保法规及税金躲得极快,工厂必须有机动性……细查其转包的历史,工厂降落在每一个新驻点的步子都越来越轻。”克莱恩指出,为了进一步压低成本,承包商甚至也会模仿跨国公司,关闭人力成本上涨的母国工厂,转而去劳动力依旧便宜的国家和地区设立新厂。
新自由主义全球竞争为那些为工资而工作的80%的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失落,数据显示,他们的工资自1973年起一直在下降。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实际上是由全球工薪族共同承担的。《新阶级社会》援引《经济学人》一篇发表于2006年的报道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化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工作,而且同时压低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工人的工资。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会的衰落。强大的工会曾是工人的筹码,迫使雇主就工资、福利和工作环境问题上做出让步,然而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统摄一切的当下,工会得不到官方支持,又被雇主污名化为侵害工人利益的存在。
有研究发现,强大的工会“有利于道德经济,使公平薪酬的规范制度化,同样惠及非工会工人”。也就是说,工会对雇主的牵制能在全社会起到树立规范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降薪裁员、福利下降不应仅仅被视为蓝领工人的困境——“节省劳动力”的铁律终将向上蔓延,威胁白领的工作保障。事实上,在把美国工厂关闭、将投资和生产移到海外以削减劳工成本后,大公司早已将注意力转向了削减中层白领雇员。《新阶级社会》指出,在1990年至2000年间,失业对拥有大学以上学历、年薪在4万美元以上的人的打击最为严重。白领员工的裁员被解释为“组织重构”,即中层管理者和监督员被追踪职员工作的新计算机系统所取代。
在《美国工厂》的结尾,一位福耀高管向前来视察的曹德旺介绍,工厂将如何通过引进机器人来取代效率依然不够高的工人。这一幕足以令不分中外的观众心中警铃大作:如果说懒散的美国工人已在勤奋的中国工人面前败下阵来,那么人工智能无疑是对所有人的降维打击——毕竟人类效率再高、再顺从听话、再踏实肯干,也比不过机器。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是最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的群体,但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也在对白领员工造成威胁。
“AI教父”尤尔根·施米徳胡贝(Jürgen Schimidhuber)在参加上海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期间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超越人类的机器终将出现,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阶段就是一台主动生成数据的机器,为所有的行业带来变革。这一前景固然激动人心,但问题是:那些被机器取代的人应该怎么办?变革推动者们或许会将这种担忧斥为21世纪的卢德主义,但当企业通过人工智能摆脱“生产工具”,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不再成立,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观念将个人成败归结为“适者生存”的个人问题时,谁还能够(或在意)保障个体的福祉?
“今天的权贵们比以前的执政精英更讲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被以各种形式灌输:不受政府束缚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文化,经济运作效率等等。在实际中,这种意识形态为许多观念提供了理由,这些观念则把少数人集中权力和财富视为合情合理的事。”《卫报》专栏作家欧文·琼斯(Owen Jones)认为,一个劲宣扬“别无选择”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极大胜利,然而一个常常被掩盖的真相是,特权阶级从中捞取了绝大多数的好处,而非保证“所有人的自由和繁荣”。

[英]欧文·琼斯 著 林永亮、高连甲 译
麦读/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 2019年6月
出路何方?我们或许应该从意识到这一点开始: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造就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巨大探底竞争,在劳资关系日益倾斜的天平之下,不掌握资本的人终将沦为“进步”的代价,无论身处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是车间工人还是办公室白领。为此,我们需要放弃某个群体是“进步代价”的思维,重视个体的尊严,挑战当下意识形态中隐藏的无限贪欲。这或许也是《美国工厂》未说出口的深意所在。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