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巴别塔》原本是圣经中的故事:人类联合起来建造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这一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互不相通的语言,彼此难以沟通。在1990年凭借《占有》获得布克奖的A.S.拜厄特(A.S.Byatt)笔下,巴别塔则成为了禁锢自由的牢笼,是令女性“失语”的传统社会。
A.S.拜厄特笔下弗雷德丽卡的故事,和今天引起广泛讨论的韩国《82年生的金智英》有相似之处。聪明桀骜的弗雷德丽卡没想到自己也会被婚姻所改变,在丈夫眼中,她只扮演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不需要自我,更不需要朋友。当她趟过婚姻的泥沼走向离婚,法官的结案陈词是:“此刻的社会并无法配合比以往更加进取的女性,也无法满足女性不断调高的期望。”弗雷德丽卡最后一搏的武器是写作,她投向了自己的第二本能——语言。她在写作过程中深恐创作欲望会被她英国文学的知识背景所禁锢,其实正如她害怕自己的爱恨和欲望完全被婚姻的教条和繁琐所禁锢一样。

《聆听与言说:巴别塔中的知识女性》
撰文 | 姚成贺(文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从1978年《园中处女》出版,直到2002年《吹口哨的女人》问世,英国当代小说家A.S.拜厄特鸿篇巨制的四部曲方才完成。其间,《静物》与《巴别塔》相继于1985年和1996年问世。四部曲围绕波特一家及相关人物的成长感悟与悲欢离合展开,尤以二女儿弗雷德丽卡·波特的经历为主线,因此又被称为“弗雷德丽卡四部曲”或“成长小说四部曲”。

《巴别塔》故事伊始,几个可能的开局就将我们带入一个塔式的螺旋结构之中。首先是画眉鸟啄食蜗牛的画面,它们引吭高歌,又仔细聆听。身后,那些背负着历史的小蜗牛,却一只只,变成空荡荡的小耳朵,再也听不到画眉之喙锤击砧板的轰鸣,再也无法安心唱出它们尖厉泠冽的歌谣。
第二个开局回到现实生活,将视线转入女主人公弗雷德丽卡的婚姻。诗人休·平克,这位在树林中思考的画眉般的自然聆听者,告诉我们失联许久的女主人公已经从一个聪明得有些狡黠的剑桥女孩,化身为戴着绿色头巾的乡郊大宅女主人,尽管眼睛还望向树林深处,却穿着错的衣服,站在错的地方,身处错的时间。
第三个开局中,主人公裘徳·梅森,故事内文本《乱言塔》的作者、弗雷德丽卡的未来同事,人未出场声先至,向身为牧师的丹尼尔·奥顿、弗雷德丽卡的姐夫发问:上帝还在吗?他相信上帝已死、随心所欲才是唯一法则。对于丹尼尔来说,聆听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也只能通过聆听来获得对裘徳的初次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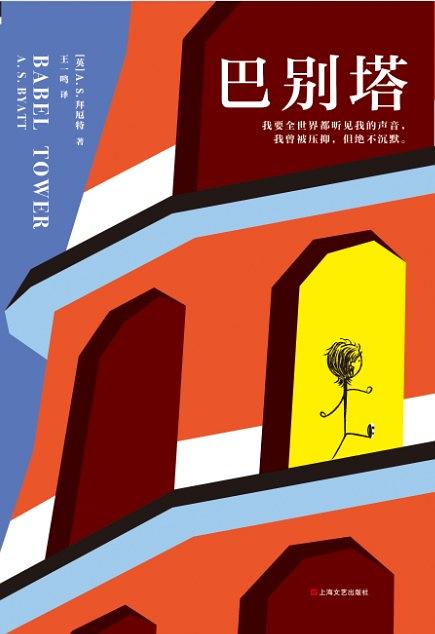
[英]A.S.拜厄特 著 王一鸣 译
读客·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10
还有第四个开局,那是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般引起诸多麻烦的《乱言塔》。一队人马穿越丛林,进入隐蔽的山谷,希冀建立真正自由的小社会。“舌之剧场”里,领导者考沃特畅叙他的自由乌托邦设想,表达了再造语言的愿望。《乱言塔》就这样镶嵌于《巴别塔》中,两条线索交错前行,令我们不断反思叙事,以及那些主宰我们人生的热情与欲望。
故事围绕着这四重开局,螺旋式地上升开来。巴别(Babel),即希伯来语中的“巴比伦”,原意为通向神的大门,但在希伯来圣经文化语境中,“巴别”意为混乱。上帝不愿人类拥有相同的语言,乃至无所不能起来,是以变乱人类的语言,使各言其言,无以沟通。“巴别” 成了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babble)。故事中的巴别塔,是弗雷德丽卡挣扎逃离的束缚之塔,也是她重新找寻自我的语言之塔;是20世纪60年代观点碰撞、左晃右摆、价值观混乱的写照;是上帝死后世界中的胡言乱语塔。如《哥林多前书》所言:
这世上声音也许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
故此,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化外之人,我也以他为化外之人。
然而,故事的主线依然是弗雷德丽卡的生活,婚姻、语言、蜗牛、教育,这些“联结”建构起巴别塔,令整个故事得以在语言编织的网中绽放。
作为女性作家和批评家,拜厄特无法对20世纪60年代女性知识分子的困惑视而不见。弗雷德丽卡的姐姐斯蒂芬妮在《静物》尾声的意外离世,几乎改变了所有人物的生活。对爱情的希冀随着姐姐的死亡而终止,弗雷德丽卡暂时蜗居在身体里。好辩、激昂、糊涂、聪颖的她嫁给了一匹与自己性格迥异、不善言辞的“黑马”奈杰尔。她一厢情愿地错误估计了婚姻的这股力量,天真地以为,“即使结了婚也不意味着要在一夜之间改变本性”。然而在丈夫眼中,她只扮演妻子、母亲的角色,不需要自我,更不需要朋友。婚姻泥沼中,弗雷德丽卡昔日那股不会止息的热情能量已然消失不见。“撑过去一天,再撑过去一天,这究竟算什么样的人生?”仙女的声音告诉她,也告诉我们,这是很多人的人生啊!
奈杰尔的观点是男权社会的普遍真理,任你婚前再聪明、独立又有野心,一旦步入婚姻,成了妻子和母亲,就应该预料到一些变化。在他们看来,你有了这么可爱的孩子、锦衣玉食豪宅,还有什么牢骚可发呢?还有什么必要去联络那些朋友尤其是男性朋友呢?连后来的离婚律师也坦言,女性在一般观念中倾向于待在家中照顾孩子。法官的结案陈词说得没错,“此刻的社会并无法配合比以往更加进取的女性,也无法满足女性不断调高的期望”。然而,“新”弗雷德丽卡躯体中那个“旧”弗雷德丽卡并不安分,自己是妻子、是母亲,同时也是“我自己”。她还想跟旧日的朋友们说说话,感受精神空间里的一点点自由。于是飞蛾扑火,向丈夫提出跟他一起出门的要求,就像赤足履过一层满铺着的煤渣,从那熏得烧得灼热的地面间隙中寻找一条通道。
出走的决心被丈夫的一句“我爱你”“我想要你”轻松化解。尽管不是一个词汇动物,奈杰尔却深谙这套爱语的技巧,随之而来的温存令弗雷德丽卡无力抵抗。她愠怒、她压制,却无法抵御身体对欲望的感知。当这种伎俩不再奏效,男人便显现出雄性动物的本性,以最原始的暴力形式撕掉隐喻的伪装,干脆利落地实施了身体上的伤害与钳制。出身书香门第的弗雷德丽卡未曾见识过人类这种野蛮的回归,语言意义上“牙尖嘴利”的野蛮力量也同样被唤起,成了伤人的武器。即便如此,弗雷德丽卡依然被故伎重施的奈杰尔招安。最终,锋利的斧头打破了温情的“联结”童话。令人唏嘘的是,逃出家门,弗雷德丽卡仍未摆脱丈夫对她身体的控制,圣诞礼物——一条朱红色的洋装,再次无声言说着一种精准的掌控,宣告奈杰尔的主权,以及弗雷德丽卡逃离的失败。

无路可逃的弗雷德丽卡投向自己的第二本能——语言,时刻准备好,在脑中招待那些由语言和光芒创造出的神话生物。于是,语言与女性的命运缠绕交织起来。弗雷德丽卡享受谈论书籍带来的乐趣,却囿于英文系的出身,深恐创作欲望会被英国文学的学习经历清空,认为自己无法写出创造性的文字。在对自己 “联结”式婚姻的反思中,她开启了写作,找寻力量的源泉。E.M.福斯特以为,散文和激情、野兽和僧人的“联结”称心如意。但他不是女人,哪里晓得“联结”的真正含义。“只有联结”,不过是欲望的神话,是对完满人生的饥渴和追求。弗雷德丽卡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对“只有联结”的追求,即使只是一点点,也的确存在于己心。哪怕准备开始接纳新的感情,对象约翰·奥托卡却同样缺失语言。唉,女人啊,又绕进另一个窘境之中,又奢望同一位数学家构筑“联结”了。
只有联结吗?疏离感难道不是一种力量吗?如果不想要“一体性”,那么还有什么?“贴合”一词击中了她的心扉。与“联结”不同,“贴合”保持了事物的疏离感。人生不是被比喻、性爱或欲望联结在一起的,而是被一贯带有着古旧知识、运行机制的事物,甚至是意外中发现的事物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并不确信,弗雷德丽卡已开始考虑,是否应该依靠写作来控制或宣泄心中的痛楚。她写下《贴合》,承认写作都是拼贴,文字的核心在于,它们一定是被使用过的,根本不必是全新的文字,终于写出了一段没有“我”的故事,让自己聆听。
《巴别塔》本身也是一个贴合起来的故事。其内文本不仅有《乱言塔》,有《贴合》,还有《霍华德庄园》和《恋爱中的女人》中的章节,教育委员会成员阿加莎的故事书《北国行》,弗雷德丽卡要写简报的小说,等等。此外,还有弗雷德丽卡在文学课上讨论的经典小说,那些谈宗教的谜语般睿智的、展现耶稣显灵般具像化语言和灵魂之力量的霍利教士的新书,利奥欲罢不能的《霍比特人》……所有这些文本的阅读与讨论。拜厄特邀请我们来聆听这个故事——这就是此刻的声音,碎片支撑起我们的一切,这就是此刻的声音,这就是极致的释放,这就是终极的真理。
螺旋式的上升结构赋予了故事蜗牛壳式的外形,一个未被画眉蚕食的蜗牛壳,背负历史的厚重。故事发生于1964年至1967年的英国,人们生活在核战的恐惧之下,自然主义者们发现成千上万只死于非命的鸟,猛烈抨击向农作物喷洒农药的行径。画眉鸟逐渐消失了,它们惨死于杀虫剂。《寂静的春天》在英国的出版,死亡的鸟类被一一列举,触目惊心。《乱言塔》中,洛绮丝女士曾聆听着画眉鸟的美妙歌声,自认为是守护这些树木的森林女神。树枝被折断,流出汩汩鲜血,凝结成绯红的血滴,无声诉说着对于人类的怨怼。人类误入歧途,亲手制造的死亡悄悄降临到空气、水中。杀死一切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才是那个“蝇王”。振聋发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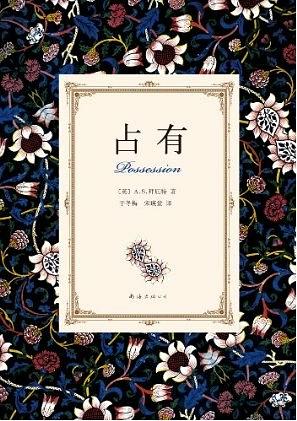
拜厄特对当代文化状况同样忧心忡忡。20世纪60年代,年轻人坚信,过去的已死,历史毁灭了独创性,他们要完成一种决裂,掀起一种反叛,创造一个新世界。连烧书都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文字虽然美妙,却已是明日黄花。书写式的文化,马上就要被贬谪到博物馆里和满布灰尘的书架上。电视像个魔术箱子,究竟以怎样的形式传播艺术和思想?在电视上,在箱子里,我们不用语言思维,而是用图像、联想和很多一闪而过的形式。连剧作家亚历山大都开始为教育电视台服务,威尔基也整天忙着他的电视游戏节目。人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嘈杂时期——道德动荡,亟待重整;混乱,却生产意义;急于重获新知。
对文化状况的关切令故事充满百科全书式的思考与回忆。在登塔的路上,我们仿佛游走在艺术学院的画廊、文学院的课堂,与弗雷德丽卡一起赏析画作,准备并讨论福斯特和劳伦斯小说中的爱情和婚姻,体会阅读的乐趣;与斯迪尔福兹语言委员会的成员们一同去小学校园调查、访谈、讨论,回忆儿时的读书经历,反思语法的教学;与杰奎琳、马库斯和卢克观察、研究蜗牛,思考环境灾难与遗传基因的问题;共同阅读《乱言塔》的书评、玛丽安娜对裘徳的访谈;旁听弗雷德丽卡的离婚案和裘徳《乱言塔》公诉案的庭审。在故事中,我们被声音包围,像主人公一样,努力辨别哪一个声音是自己的。
拜厄特在书中提醒读者,小说都是由一长串的语言建构而成,就像编织。在法庭上,弗雷德丽卡和裘徳都需要复诵各自人生故事的滑稽模仿。人生的叙事何尝不是如此?人生的叙事也是一张网,它定义着也改变着每一个人。阅读和写作对人类如此重要,聆听与言说故事是人类最原始的交流方式。劳伦斯说,小说是人类表达思想情感方式中的最高形式。在文字中,画眉鸟依然歌唱,你,是否在聆听?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