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弗·南苏加·马昆比(Jennifer Nansubuga Makumbi)于1967年出生于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现居英国曼彻斯特。她的第一本小说《肯图》(Kintu,乌干达创世神话中的生物)于2014年入选阿联酋电信文学奖(Etisalat Prize for Literature,现称为9mobile Prize for Literature。一个泛非洲文学奖项)长名单,并于同年获得英联邦短篇小说奖。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Manchester Happened》2019年出版。2018年,其小说赢得了温德姆·坎贝尔奖(Windham-Campbell prize)。她的新书《第一个女人》(The First Woman,暂译)从女权主义视角出发演绎了乌干达的起源故事,讲述了少女Kirabo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旅程。
“有母亲的感觉如何?”这是本书核心的问题之一。
马昆比:直到十岁左右,我才第一次和母亲见面。在那之前,我常常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小时候,我和父亲住在一起,但是他在伊迪·阿明当政期间遭受残酷折磨,后来精神失常,所以大概10岁左右,我开始和姑妈一起生活。我想探讨的是这样一种经历——当你没有母亲时,你会在脑海中创造出一位母亲,并将她想象成一个完美的女神。当Kirabo遇见她的母亲时,她哀悼自己失去了的、想象中的母亲。这是我想描绘的那种经历。
在致谢中,你感谢了母亲伊夫琳。你说,“她分享了她的家族史,以及她的村庄的历史。”
马昆比:《肯图》的背景主要基于我父亲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第一个女人》的背景则是我母亲出生的地方。她没法读书,因为她不懂英语,但她向我详细讲述了我们的祖先遭受的苦难。学校并没有教过我这一部分历史,这使得(乌干达的)很多人都不了解他们所在的地区。
你直言不讳地描述了残酷专政对乌干达的影响。

马昆比:这本书的背景始于1975年,即伊迪·阿明将亚洲人从乌干达驱逐出国的三年之后。小时候,我知道亚洲人在被驱逐期间自杀,他们迁到了尼罗河的源头区域。人们以为他们可以回到印度,但他们出生在乌干达,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很多亚洲人被带到肯尼亚和乌干达,以契约劳工的身份工作。在学校里教授这一段历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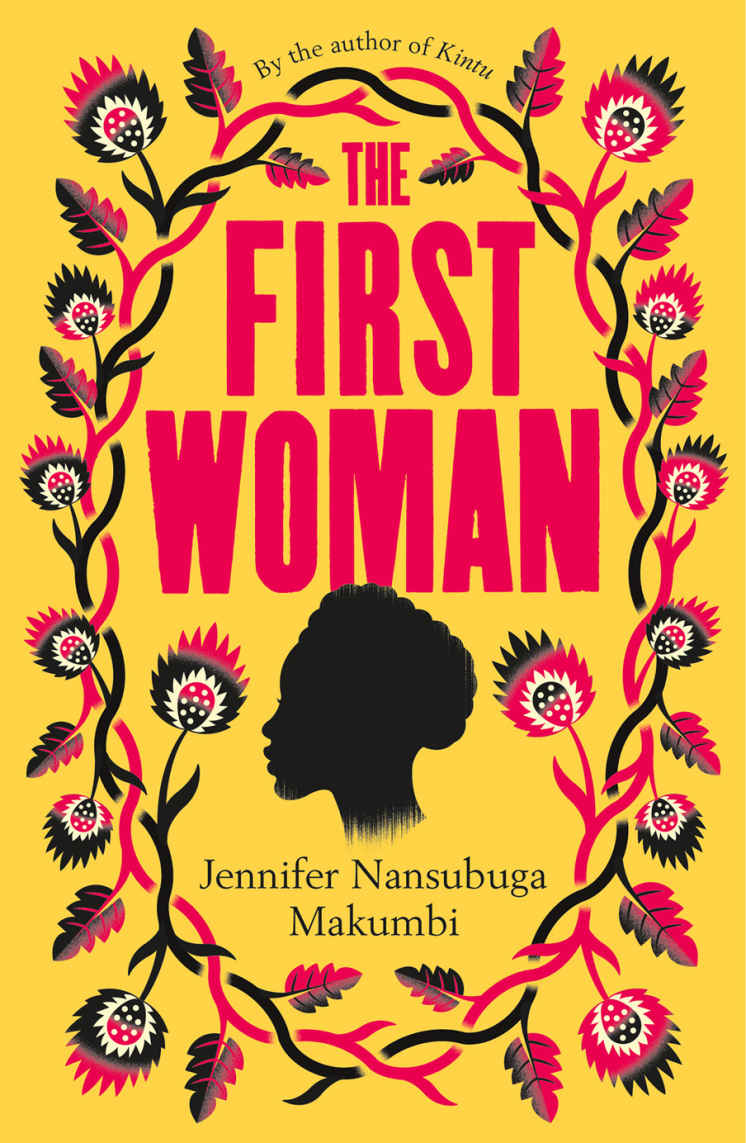
在整部作品中,家这一主题很抢眼。
马昆比:我必须写一写曼彻斯特,是曼彻斯特收容了我。我知道自己有故事,但我需要学习讲故事的技能,于是我开始学习创意写作。《第一个女人》是我为文学硕士项目写的。地点的写作对我很重要,一个地点本身就能讲述很多故事。
你的大部分作品都以民族学为核心之一。
马昆比:小时候在假期里,我与祖父母住在一起。他们会在晚上给我讲故事,所以我很早就开始接触故事了。我决定,即便我写的东西是文学性的,我还是会专注于故事这一概念。这可能是因为我接触到故事的契机是口传的民间故事和童话。吸引读者的娱乐元素与故事要传达的信息一样重要。
你向读者介绍了比西方女性主义更早的本土女性主义。
马昆比:这是我的主要意图。这一切都记录在我们的民间故事和口述传统中。由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女性之间的差异,女权主义无法在乌干达生根发芽。如果女权主义在乌干达无法取得进展,我们应当回头看看我们的女性祖先留下的东西。为了探讨女性受到的压迫,我需要追根溯源,探讨女性是如何被压迫的。
Kirabo了解到了迷思(myth)的力量。
马昆比:生活就是创造迷思。我们会不断在自己周围创造迷思,因为我们希望人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看到我们。我们围绕个人、社会和族群创造迷思。问题在于,有太多破坏性的迷思被用来压倒女性,例如“女性在生完孩子后会失去部分大脑”。创造迷思是寻找声音的一种工具。
你小时候是怎样一个读者?
马昆比:我会读到忘记吃饭;如果是做饭的时候读,菜都会烧糊。我记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那时我大约12、13岁,我很喜欢米尔斯‧布恩(Mills&Boons,英国著名言情小说出版商)的书。读书的时候,我会沉浸在书中的世界。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奇努阿·阿契贝的《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因为我父亲有很多书,那时候我仍然和我父亲住在一起。我会在其中找到最薄的一卷,然后读它。整本书有浓郁的非洲色彩,书中的元素甚至可以在我的村庄里被找到。
你的床头柜上有什么书?
马昆比:现在我正在读马龙·詹姆斯(Marlon James)的《黑豹,红狼》(Black Leopard, Red Wolf),我真的很喜欢这本书。我在我的出版商那里拿了几本书,所以我有黛安娜·库克的《新荒野》(The New Wilderness)和尼科尔·丹尼斯-巴恩(Nicole Dennis-Benn)的《傻瓜》(Patsy)。
哪些作家影响了你?
马昆比:在成长过程中,我并不曾认为自己会成为作家。但要回想起来,《肯图》的灵感来自塞内加尔作家、电影制片人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ène)的《上帝的木屑》(God's Bits of Wood,暂译)。后来,我发现了托妮·莫里森。她一直提醒我,你不能直接就这么写下一个句子,你得反复斟酌它。爱丽丝·沃克对我也有影响。伊冯娜·维拉(Yvonne Vera)的大胆振奋人心,她写下了很多难以言喻的东西。齐齐·丹加伦加(Tsitsi Dangarembga)的《紧张状况》(Nervous Conditions,暂译)也对我有影响。
你有固定的写作流程吗?
马昆比:没有。在写故事之前,我往往会花很多时间在脑海中构思。片段不停地浮现在我的脑中,我需要重组它们,所以当我落笔把它们写下来时,我已经明确了写作的方向和路径。我写东西甚至有些强迫症倾向。如果我有东西要写,在停笔之前我就会一直一直写。
(翻译:王宁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