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莫素德(Claire Messud)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父亲是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母亲是加拿大人。莫素德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了她的丈夫,作家兼评论家詹姆斯·伍兹(James Wood)。现在,莫素德在哈佛大学任教,他和丈夫、两个孩子以及两只小猎犬共同生活在马萨诸塞州。
同时身为小说家的莫素德著有7部小说,其中包括入围布克小说奖的著作《皇帝的孩子》(The Emperor's Children)和《燃烧的女孩》(The Burning Girl)。上个月,莫素德出版了新书《康德的“普鲁士小脑袋”,以及我写作的其他原因》(Kant's Little Prussian Head and Other Reasons Why I Write),收集了她过去20年间的随笔和书评。
这本新书的书名很有意思,是有什么说法吗?
克莱尔·莫素德:我的灵感来源于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一篇文章。事实上,我想表达的就是,每读一本书,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书中所有的东西。或许你在一个月或是一年前读过一本书,当你再回想起来的时候,你想起的都是精华部分——有时候是一个图像,一个场景,或是某个情节中的一个瞬间,甚至是某篇文章中的一个想法。你不会主动地去记住所有细节,至少不会去有意识地记住全部。正如我爸爸过去常常说的一句话:文化就是当你忘记所有之后留下来的东西。
在你的随笔中,你的母亲经常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她与痴呆症的抗争是否影响了你对记忆的想法?
克莱尔·莫素德:早期做脑部手术的时候——你也知道,做脑部手术的时候病人是清醒的——通过多次刺激到病人的小脑,他们意识到,人的所有记忆就储存在那里。当他们刺激到某个位置时,病人会说:“我和爸妈在湖面上的一只小船里,我那时候9岁,这是空气的味道。” 我母亲患的是一种特殊的痴呆症——路易小体(Lewy bodies)。有人是这么跟我解释的:“老年痴呆症就像是一把锁,锁住了记忆的文件柜,而路易小体则正好相反,它把记忆的文件柜打翻在地。”但是不管怎么样,记忆总是储存在那里的。这和我们读完一本书之后的记忆是一样的,你或许一时想不起全部内容,但是它们就在那里。就像是普鲁斯特的瞬间(Proust and his madeleine),那一口玛德莲复苏了他多年束之高阁的记忆。你也不知道那些你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情或是在书中读到过的情节,是否会在某一个瞬间会被唤醒。

你总是说自己是混血儿,那你觉得这个身份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帮助,又有什么阻碍呢?
克莱尔·莫素德:这一点我也思考了很久。在某种程度上,身为一个作家就是要把自己抽离出来,做一个旁观者。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切哲学都是神经病。如果你没有点神经质,那么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写的,不过是匆匆过活罢了。我很欣赏爱丽丝·门罗的作品,而她对于住处要求非常严格:她住的地方离她上学的地方就很近。我也看好萨尔曼·鲁西迪的《想象的家园》。哪怕你只是搬到离家乡一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你也再不会回去。你离开的那个地方就和离开了的你一样,不断在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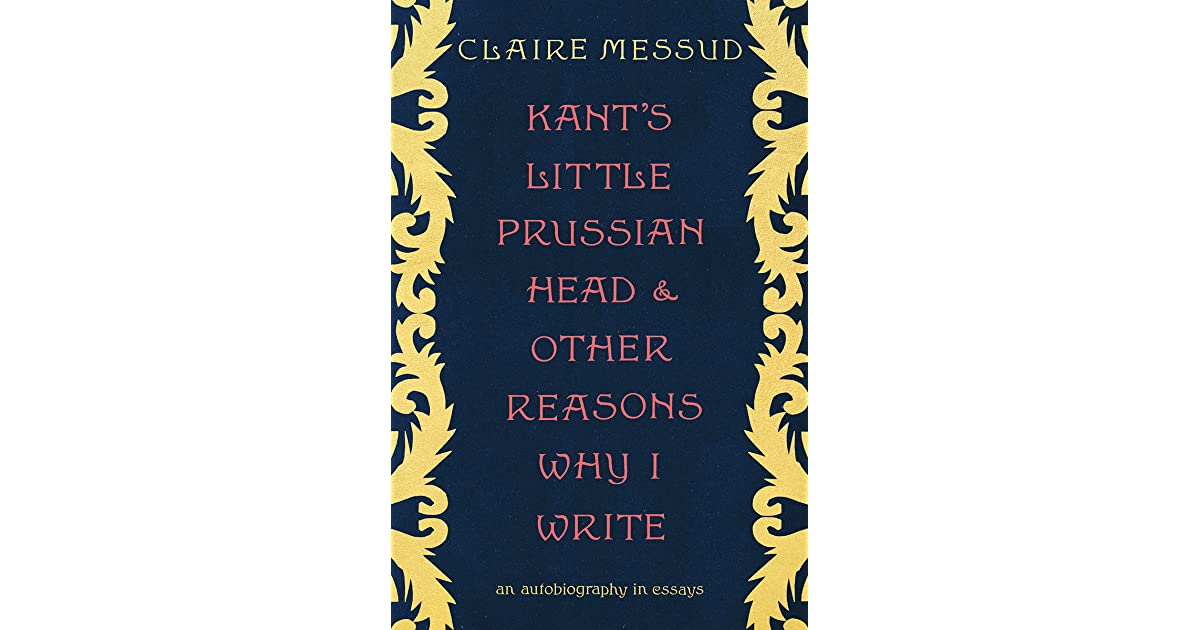
你的新书里面有一篇文章,《青春期女孩》(Teenage Girls),是关于你的女儿和她的朋友的。这些是不是就是你创作《燃烧的女孩》的素材呢?
克莱尔·莫素德:我之所以写《燃烧的女孩》这本小说,一方面是因为我有一个十几岁大的女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经常开车带她和她的朋友出去玩。很有趣的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似乎是不存在的,你就像是个俄罗斯司机——他们觉得你根本就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你幸运的话,往往在这种时候你就能看到,当你不在的时候他们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我曾经有想过,把我年轻时的经历写成一个虚构的故事。洛丽·摩尔曾为一本青少年题材的作品做书评,她形容青春期就是一只咆哮的狗;最终,这只狗被埋了,而且是被活埋。我发现,当我以“家长”的身份经历我女儿的青春期时,这些“被活埋在内心的咆哮”复苏了。
你定期为《纽约书评》写书评,其中当然会有些差评。你会怎么去面对那些被你给过差评的作家呢?
克莱尔·莫素德:我记得几年前在伦敦参加过一次聚会,我介绍两个人互相认识,却不知道其中一个曾经评论过另外一个人,而且评论的话可不怎么客气。他们见面的时候,被评论的作家看着写评论的人说:“原来,我没想到你这么胖。”
现在,身为一个作家,我很清楚只会有两种评论:一种是单纯评论作品的好与坏,还有一种则是评论作者本身是否想要通过作品达到什么目的。如果是后者,我会非常感激。如果评论人丝毫没有感受到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我可能会感到受伤或是难过,但是只要他们能够试着去理解我想做的事情,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拿《燃烧的女孩》举例来说,很多美国的评论家一开口都是“这是一本不可思议的小说”。你可以说这是好的评论或者不好的评论,但是对我而言:“嗯,这说了等于没说。”所以当我的身份变成一个评论家,我想努力做到的就是:尽量不去问“我喜欢这部作品吗”这样的主观问题,而是去思考“作品本身,以及作者通过作品想要表达什么”。
你的床头柜上有哪些书?
克莱尔·莫素德:有雅克·阿塔利的《1943年阿尔及尔,欺骗之年》(L’Année des Dupes Alger 1943)、维斯瓦娃·辛波丝卡的《辛波斯卡诗选》(Map: Collected and Last Poems)、马萨·蒙吉斯特的《影子国王》(The Shadow King),非常精彩的小说,等等。实在是太多了,没办法一一列举。
你是怎么整理你的书的呢?
克莱尔·莫素德:以前我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不过现在要是想找一本书就只能靠猜了,因为书和书摞在一起早已经成堆了。
如果纯粹作为消遣,你会读什么书?
克莱尔·莫素德:疫情隔离期间,我们一直在读托尔斯泰的书。小说家李翊云在网上也组织了一个《战争与和平》读书小组。平时,我、詹姆斯和孩子们也会坐在餐桌旁一起读《安娜·卡列尼娜》。
如果要你推荐一本书给一个12岁的孩子,你会选择哪本书?
克莱尔·莫素德:达夫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
(翻译:刘桑)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