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的传记作家问到“你什么时候最快乐”时,菲利普·罗斯会想起他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第一年,那时他可以自由地追求他那执着的“拜伦式梦想”:“白天围着书目转,夜晚围着女人转。”布莱克·贝利在引人入胜的罗斯传记《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里揭示,在接下来的60年里,由于罗斯经常感到沮丧,有时甚至精神错乱,这种理想化的日程安排通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打了折扣。在芝加哥,以及随后始于迪克斯堡的两年服役期间,他第一个迷恋的情人玛克辛·格罗夫斯基经常来看望他,他深情地向贝利回忆道,他们见面时总是在门口扯下对方的衣服。“我很久没有这样做了,”79岁的罗斯若有所思地说,“我仔细地脱掉衣服,把它们挂起来,然后躺到床上看书。我喜欢这样,就像我喜欢扯下衣服一样。”罗斯晚年欲望的解放,造就了这本900页的传记。
罗斯一生中两次巨大而持久的创伤是他的婚姻。先是跟玛格丽特·马丁森,一个大他五岁的女服务员,他最初引诱她是为了“测试”自己能否吸引一个“希克萨金发女郎”(非犹太姑娘——译注),随后贝利借用罗斯的眼光形容她是“一个怨恨的、贫穷的、没有性吸引力的离婚女人”。马丁森用欺骗的方式逼他结了婚,她谎称自己怀孕了,花3美元从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孕妇那买来了一份尿样作为证据,并威胁说,如果罗斯离开她,她就自杀。第二个“陷阱”是与演员克莱尔·布鲁姆的婚姻,从1975年起,罗斯与她共同生活了近20年。她在回忆录《离开玩偶之家》(Leaving a Doll's House)中记录了那些时光,无情地批评了罗斯在这段抓马剧中的角色。
从这些痛苦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后,罗斯的写作生涯取得了两次重大突破。《波特诺伊的怨诉》是在马丁森死于车祸后迅速完成的,此前他与马丁森早已离婚,但从未获得自由。这本极其趣味的书是他所有“成长”小说中最直白的一部,也是他的出版商兰登书屋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这让罗斯成为保守犹太社区眼中的耻辱,但同时也让他获得了财务自由。
他虚构的自我经常以最糟糕的一面展现罗斯。“有何不可呢?”他问,“文学又不是道德上的选美比赛。”
他在文学上的第二大突破,正值他从与布鲁姆分手前的精神崩溃中恢复过来(在考虑过自杀后,60岁的他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布鲁姆去探望他时,她也被注射了镇定剂,并得到了一张床)。罗斯的解放,首先体现在1955年出版的《萨巴斯的剧院》(Sabbath's Theater)中大量的男性生殖器描绘,然后是无与伦比的“美国三部曲”,以《美国牧歌》为开端,三部曲为罗斯赢得了各大奖项——除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是他应得的,也是他梦寐以求的(贝利指出,多年来,一年一度“在斯德哥尔摩玩乐”似乎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忽视罗斯)。

[美]菲利普·罗斯 著 罗小云 译
译林出版社 2011-1
在他中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的虚构对象是他自己,他尝试书写了各种各样的第二自我。正如贝利在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在很多方面,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多面体。他对朋友和家人怀有极大的善意,但在追求艺术时也表现出惊人的自私;他可能是最好的伙伴,也可能是最糟糕的(“我知道,如果我没有稳定地写作,共同生活时我就是一个可怕的人。”)。他植根于年轻时生活的纽瓦克的小镇价值观,但在无情摧毁这些价值观时毫无愧疚之心(令他父亲惊愕的是,他在成年礼后第二天就宣布放弃犹太教,随后宣布他的信仰是“风流的幽默作家”)。贝利指出,罗斯虚构的自我,即内森·祖克曼及其他人,往往展现了罗斯最为糟糕的一面。“有何不可呢?”罗斯问道,“文学又不是道德上的选美比赛。”

如果说他受制于自己的力比多,那么他也受制于发挥自己身为作家的天赋所需的种种要求。罗斯将写小说的永无止境的“过度投入”描述为一种“杀死你、同时突然成就你”的高强度行为。贝利观察到,濒临死亡时,在夜晚,罗斯会躺在床上,试图记起他认识的每一个人,“出于古老的习惯”写下他们,然后如释重负地回顾说,他不再“日日夜夜地听从他的才华的要求”。
罗斯推荐贝利当他的传记作者,因为贝利为另一个自我毁灭的讲真话者约翰·契弗写了一本犀利而富有同情心的书。“我不希望你为我正名,”罗斯告诉他,“只要让我有趣就行。”在保留道德判断的同时,贝利恰如其分地给罗斯想要呈现的“作为一个人的生活”的“事实”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深度和背景。也许,他有时会感到内疚,因为他对罗斯所描述的那种伟大的男性激情看得有点过于认真了。罗斯不成熟的迷恋和变心得到了包容,但被抛弃的情人们和她们被颠覆的生活有时会被含蓄地斥为乏味或歇斯底里。一个酗酒并有自杀倾向的年轻情人“西尔维娅”,诱使罗斯成为一个“文化原始人”,而其他无数关系让他沉迷于《窈窕淑女》那种养成式爱情的幻想之中。因加·拉森(化名)是《萨巴斯剧院》中米奇·萨巴斯的欲望对象的原型,她与罗斯有着长达18年的恋情,当她与丈夫离婚并搬去跟他同住,这段恋情便结束了。罗斯在一封信中写道:“她是个很棒的偷情对象,但不是很好的伴侣。”“可以说,罗斯也是如此,”这句是贝利的评价(“可以说”是他那本文笔精美的作品中为数不多几个多余的词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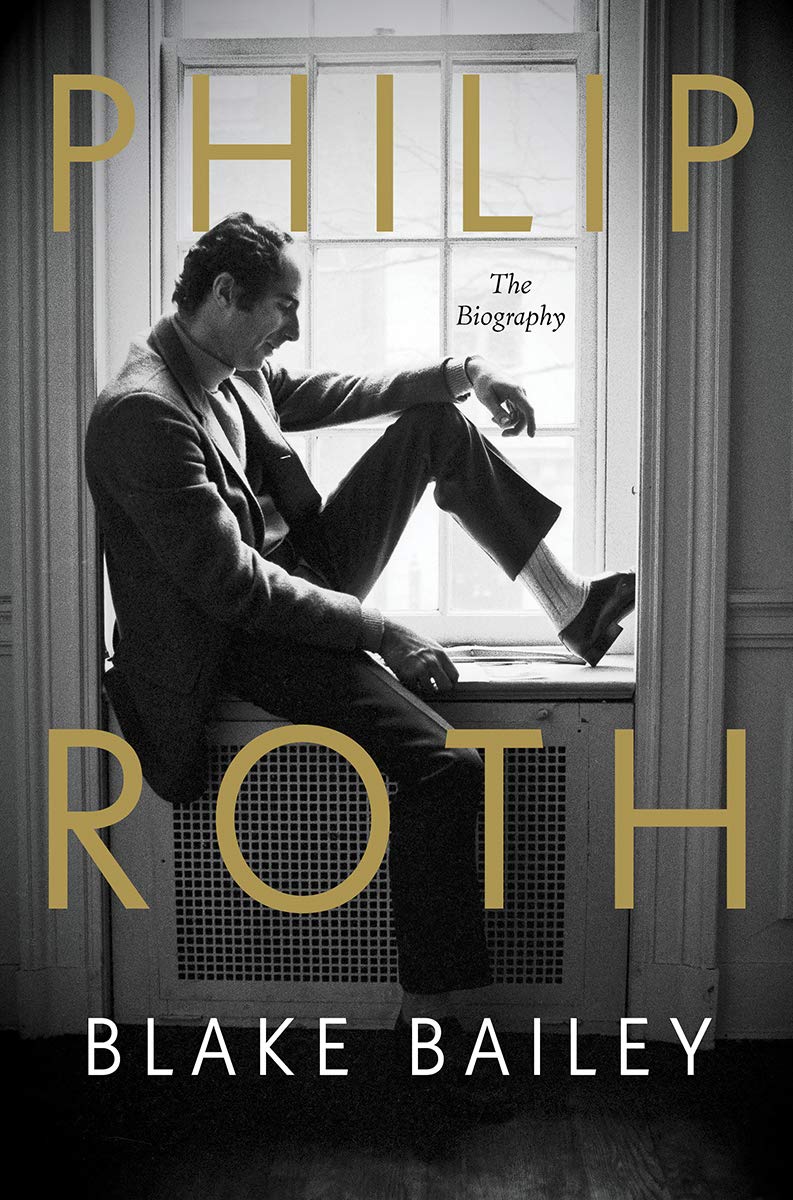
罗斯没有自己的孩子,这是他一生中的奇怪之处(也可能是悲哀之处)——尤其是因为他在31本书中塞满了大量的紧急性行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前情人朱莉娅·戈利尔的一对年轻双胞胎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戈利尔成为了他的共同遗嘱执行人。他最后的遗言是在医院病床边对戈利尔说的,“我爱你的孩子,”罗斯说,“他们是我生命中的快乐。”在遗嘱中,罗斯给他们留下了一笔不菲的遗产。剩下的大部分都捐给了纽瓦克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从未离开过他的问题:“是什么让我成为了作家?”很难想象还有哪本书能给出比这本书更明确的一系列答案。
(翻译:刘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