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与18世纪,一群西方哲学家之间爆发了冲突(至少在纸面上如此),争论围绕古老的罪恶问题(problem of evil)展开:即一个善的上帝何以能允许世上存在罪恶与苦难。哲学家如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和莱布尼茨,以及后来的伏尔泰、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这些泰斗级人物,不仅在这一问题如何能得到解决上各执己见——假定它可以得到解决的话,在如何谈论此类阴暗事物上亦有尖锐分歧。
生活还能否得到辩护?
在现代人眼里,这些“神义论”(theodicy,企图为创生作辩护)论证可能跟古代文物差不多,但在一个年轻人开始追问把新生的小孩带进这个世界的道德性的时代,它们却十分应景。说到底,问题不只关乎上帝,它关乎创生(creation)——更具体地说,就是给定世界上存在着弊病或“罪恶”这一点,创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得到辩护。

创生问题对如今的我们而言颇显紧迫。考虑到气候危机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在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何种未来的情况下创造新人,能否得到辩护?如果可以的话,辩护的限度又在何处?大部分人可能会同意,我们可以设想一些世界,创生在其中将是不道德的。生活之恶劣或其不确定性会在哪个临界点上达到不值得一过的程度?
当然,启蒙运动早期也还没有此类对地球未来的关切。但还有一些生活(existence,该词有强调人类生活中的烦恼及无趣一面的意味——译注)之中的各种罪恶,且为数不少,如犯罪、不幸、死亡、疾病、地震以及生活本身的酸甜苦辣。考虑到这些罪恶,这些哲学家追问道:生活还能否得到辩护?
这一旷日持久的哲学争论正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这两大术语的来源,它们在现代文化里运用极多,滥用也不见得少。“乐观主义”是耶稣会(The Jesuits)给莱布尼茨等哲学家贴的标签,他主张我们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里最好的”(原因是如果上帝可以造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他显然早就会这么做了)。不久后,伏尔泰等哲学家成了“悲观主义”的代表,他的小说《老实人》历数世上的诸多罪恶,讽刺了莱布尼茨式的乐观主义。“如果这就是所有可能世界里最好的一个,”伏尔泰笔下的主角这样问道,“那其它世界得坏成什么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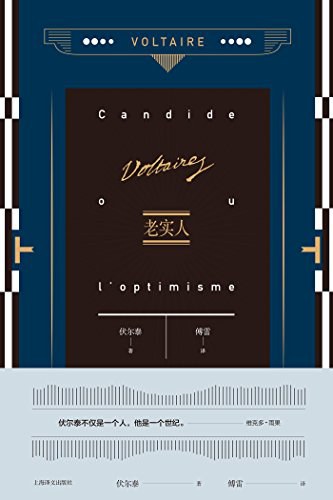
[法]伏尔泰 著 傅雷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8
但伏尔泰实际上不算悲观主义者,其他哲学家如贝尔和休谟在论述生活的坏处上走得要远得多。对贝尔以及随后的休谟而言,关键不仅在于生活中的罪恶在数量上比善要多(虽然他们相信这也是事实),还在于这种多具有压倒性。一种生活里的善恶时刻可能在次数上相等,但问题是,恶的时刻通常有一种足以使天平发生倾斜的强度。贝尔认为,一小段时间的坏便足以让更大数量的好付诸东流,正如一点海水就可以让一整桶新鲜淡水变咸。与此类似,一个小时的深切悲伤所含的罪恶,也要多于六七天的高兴日子里蕴含的善好。
莱布尼茨与让-雅克·卢梭等思想家则反对这种冷峻的看法,他们强调的是生活里的善,以及我们在一切事物中寻求善好的能力。如果我们能调整自己的视角,便能看到生活其实是非常好的:“在人的一生里,善好之多乃是罪恶无法比拟的,正如住房之多也是监狱无法比拟的,”莱布尼茨写道,“如果我们能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世界便能服务于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就能在其中感到幸福。”正如悲观主义者相信乐观主义者坚守生活之善乃是被蒙骗了,乐观主义者也认为悲观主义者戴着一副只看坏事的有色眼镜——每一方都批评另一方没有采纳正确的视角。
因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什么是正确的视角?
乐观悲观只因视角不同?
随着对这些问题的钻研愈发深入,我(指本文作者Mara van der Lugtis)开始注意到,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都高度关注理论论证背后的伦理预设。问题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创生能否得到辩护?但在其之下,还有一个从未远去且更加深刻、伦理与情感色彩都极强的问题:如何以一种能够提供希望与安慰的方式来谈论苦难?
双方对论敌的抨击都不只是理论上的,也是道德上的。从根本上来说,悲观主义者对乐观主义的最大不满在于,即便面对严酷而持久的痛苦,他们也坚持认为生活是善的,或者认定我们可以左右自己的幸福,“只要我们愿意”就能得到幸福。而这只会让我们的苦难更趋恶化,因为这是在苦难之上再加了一层对于苦难的责任,是让受苦之人再背上缺失感(sense of inadequacy)的负担。如果生活如此良善,那受苦之人面对的考验就必定源自其错误的视角,事实上,乐观主义者也确实倾向于类似的表述。悲观主义者声称,这解释了乐观主义何以是一种残酷的哲学——就算它给了我们些许希望,那也在安慰方面失败了。

但从乐观主义者的立场看,他们其实也有相似的关切。他们反对悲观主义者的点在于,假如我们坚持苦难是强烈、无处不在且无可逃避的,如果我们竭力渲染其深重与冷峻(正如悲观主义者事实上的惯常做法那样),那也是在给苦难加码——这只会让苦难变得更糟,因为“给予罪恶以本来不应有的关注,只会令它倍增”, 莱布尼茨如是说。乐观主义者声称,悲观主义本身就是反安慰的,在此之外,它还在渲染无望。
既如此,这些哲学家心系的问题,就不仅是从理论上看生活总体而言是好是坏,而是一件更具体而微的事:面对受苦之人,哲学能带给他们什么?哲学可以在希望与安慰方面提供哪些助力?
非此即彼的选择?
两大思想流派的目的一致,但规划的路径却不同。悲观主义者提供安慰的方式,是强调我们的脆弱性,以及承认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可能得不到幸福,毕竟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与之相比,乐观主义者则强调我们的能力,主张无论处境有多么黑暗和冷峻,我们都总是能改变自己的图景与导向,我们总是能对准更美好的东西前进。
当然,这两条路线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不可调和之处,每一方都可以作为另一方的必要对立面,都可以减轻对方因用药过量而产生的毒性。但事实是,早期的悲观主义者与乐观主义者的确把彼此看成是对立的,我们也是一样,仍旧倾向于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看待二者,俨然过生活就要在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之间做出艰难抉择,或者用诺姆·乔姆斯基的话说,要么乐观要么绝望:
我们的选择有二。我们可以悲观、打退堂鼓然后任由坏事发生。我们也可以乐观、抓住那些确实存在的机遇进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哪有什么好选的。
这个例子足以表明我们在使用这些术语时的粗放与片面。乐观主义一般会被赋予积极色彩,而悲观主义则充满消极色彩。我们说一个人是乐观主义者,一般都是称赞。这就是为什么政客尤其爱宣称自己是乐观主义者,甚至还谈到所谓“乐观主义的义务”。反之,说一个人是悲观主义者,一般都是对他的嘲讽、谴责和奚落。“悲观主义是失败者的专利,”如同某新书的标题所言。

但我们的选择真的有这么非此即彼吗?如果悲观主义之路愁云惨淡,那乐观主义之路也暗藏杀机。且这些危险都是老一辈悲观主义者反复警告我们的:假如我们过分突出自己掌控自身心灵、生活与命运的能力,那陷入残酷境地也就是须臾之间的事。
悲观主义不等于消极
我们用不着举更多例子来说明乐观主义的最坏形式会有什么下场了。2008年,当一座名为“海盖特庄园”(Heygate Estate)的塔楼被卖给外国投资者时,其中的居民首先遭到了驱逐,然后由当地议会向其提供正念课程,以缓和他们的焦虑,这样一来他们就得自己为自己的不幸负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彻底地控制自己的精神状态,那要求社会正义的理由又在哪里?这一阴暗面向与“你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的流行叙事密不可分,而社交媒体的运作机制又以润物细无声的恐吓,使得这一叙事更趋强化,迫使我们向全世界播报自己的成功和幸福。
这些情形充分体现了悲观主义的安慰力量:状态不好也没关系。我们有时会失败,我们有时又会因自身能力或世界的界限而碰壁。同样能抚慰人心的提示是,我们的脆弱性不是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痛苦并非咎由自取。因我们正在、暂未或业已失去的东西而悲伤不已,也可以是正当的。
我们很容易就会把悲观主义等同于消极、宿命论或绝望,然后彻头彻尾地拒斥它——我们当然不想要一种劝告我们放弃的哲学。但悲观主义真的提倡这些吗?如乔舒亚·福阿·丁斯塔格(Joshua Foa Dienstag)就在《悲观主义:哲学、伦理与精神》(Pessimism: Philosophy, Ethic, Spirit)里指出,悲观主义并不会导致消极倾向,它与某种道德与政治行动主义的传统有紧密的联系,以阿尔贝·加缪为例,他在二战中的勇敢和积极行动就源自其悲观主义理念。

即便最幽暗的悲观主义者也从来不会说生活只会变差或者绝无可能变好:这是对悲观主义的漫画化处理,草草勾勒一番只是为了打发它。即便是亚瑟·叔本华这种最冷峻的悲观主义者,也不会持有上述观点。相反,他主张正因为我们无法控制事态进展,我们也就永远不知道未来的样貌:生活既可能变坏也可能变好。”用丁斯塔格的话说,“悲观主义者不抱任何期待。”这么说可能显得不给人希望,但它本身又是某种形式的希望。同样地,这些作者最阴暗的篇章仍透出了些许微光:如敏锐而不安地察觉到在黑暗的图景之中也可有所收获,又如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拓展眼界,再如我们也许能在黑暗中看清一些东西。
这表明了怀有希望的悲观主义(hopeful pessimism)何以不是自相矛盾的,而是一种野性力量的展现,只有将生命中最为黑暗的力量汇入希望的奇妙炼金术,我们才有望驾驭它。
指责年轻人悲观毫无道理
在我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生态耗竭与破坏、始料未及的洪水与山火、突破历史峰值的气温以及阴魂不散的气候危机正困扰着这个时代。年轻人安静或不那么安静地陷入绝望,则是当代的另一特征。以往悲观主义者所受的批评,如今又原封不动地被技术乐观主义者与进步的鼓吹者用来指责年轻人,在这两类人眼里,单单考虑一下衰败的可能,就已经是软弱、想象力不足以及道德缺陷的标志——说到底是图景有问题。他们还以类似的口吻,抨击年轻人的抗议是悲观主义、宿命论、“一味地”绝望。他们批评年轻人信奉的图景太冷峻、论断太夸张、发声者太娇生惯养。
以下的事实被轻描淡写地打发掉了:这代年轻人——在一个气候危机不仅初露端倪、而且已经是严峻现实的世界长大的第一代人——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将会失去未来,他们被灌输的一切赋予人生以意义的事物,如今不是变得空虚就是出了问题。诸如此类的事情:学习,找个好工作,安顿下来——然而还有什么工作是确定的?哪里还有安居之处?格蕾塔·桑伯格2018年曾在伦敦议会广场有言:“在没有一个人愿意采取措施挽救未来的情况下,我凭什么要为一个很快就不复存在的未来而学习?”诸如此类的事情:成家——但如果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未来,生育还有什么意义?即便像通过旅行来增长见识这些更加琐碎的事情,也不再是一目了然的了:和一次现代旅行所耗费的碳相比,自我发展又能有多重要?

这一意义的全盘崩塌只是在最近才变得明晰起来的。年轻人经历的真实感受,是自己不仅丧失了对未来的概念把握,还丧失了未来本身,“是什么令生活值得一过”这个问题的种种寻常答案,都已变得愈发不确定。他们身处那一黑暗之中,搜寻着某种希望以及安慰——我们又能给他们什么呢?比起给出一些显然很苍白的答案(这些答案还可能干脆就是谎言)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我们明白事态很有可能好不了——我们还可以有更多建树。
任何简单粗暴的乐观主义论断,其弊端都不止于不合时宜,它还是一通谁也骗不了的谎言,起码所有怀抱敏锐道德感的年轻人都不会上当,他们早就看透了政客们的空洞承诺与保证,他们的愤怒也是正当的。假如我们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那就连说空话都还不如了。如此一来年轻人就无法认真对待自己的经验,且正如悲观主义者所言,这样做只会加剧他们的痛苦。
悲观主义是一种德性
但如果朴素的乐观主义失败了——悲观主义就能做得更好吗?我曾经提出,悲观主义也有其价值——但我们能否走得更远?它能否在事实上成为一种德性(virtue)?
对一些人而言,说悲观主义是一种德性本身就显得荒唐。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诉诸休谟的观点,即任何德性的标志都在于它是有用的、宜人的,且对拥有它的人以及其他人而言都是如此,但悲观主义当然是既无用也不宜人的。它之所以无用,是因为它使我们趋于消极,不仅压抑我们自己,也如同玛丽琳·罗宾逊(Marilynne Robinson)在评价文化悲观主义时所言,压制“我们对可能之事的感受力”。它之所以不宜人,是因为它加剧了我们的痛苦,使我们专注于生活里坏的一面而非好的一面(诸如莱布尼茨和卢梭这样的乐观主义先驱就会这么看)。既如此,一些有关所谓“道德模范”的研究将积极、充满希望以及乐观主义列为道德典范的共同特征,也就不足为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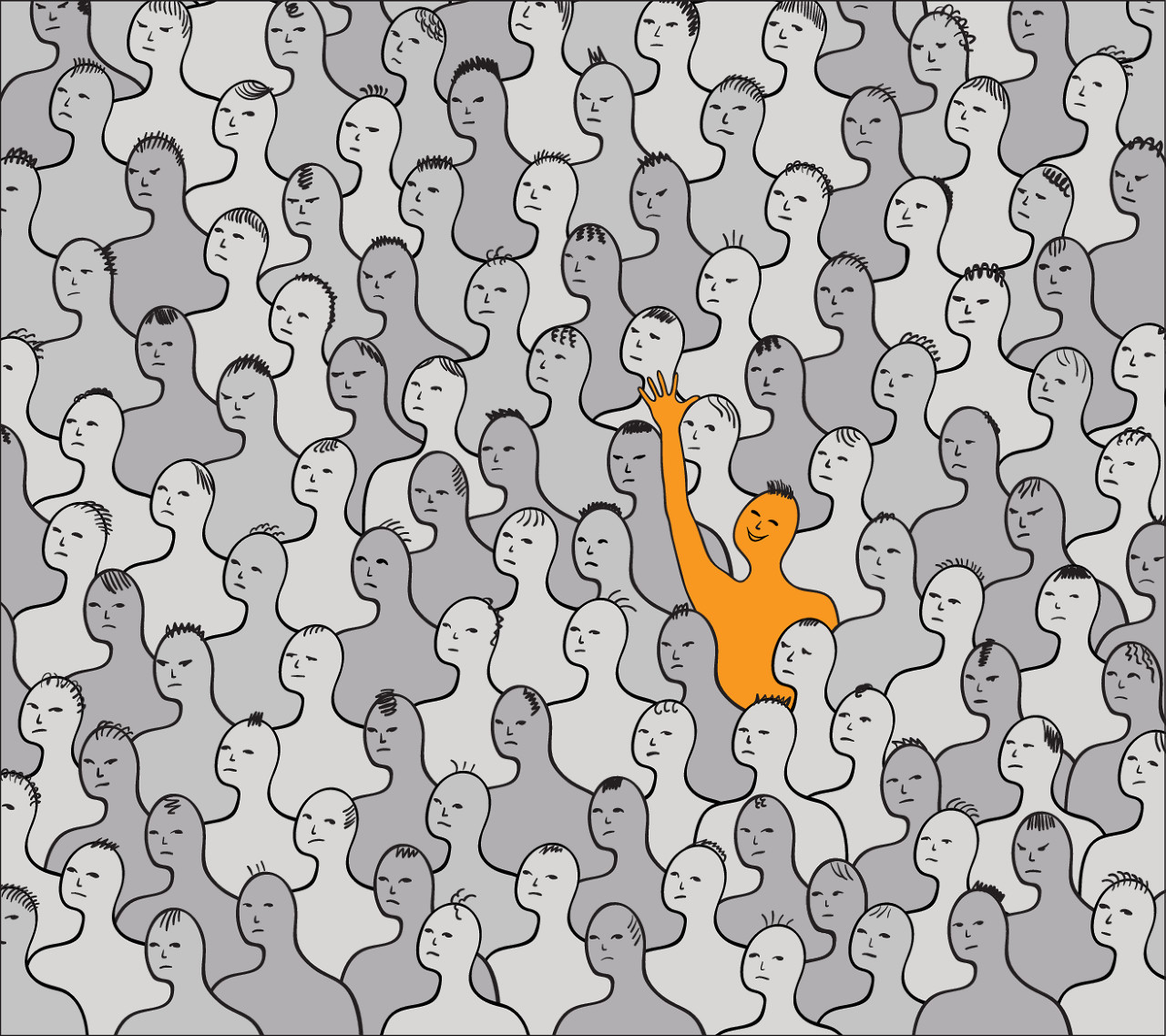
回过头来谈一谈格蕾塔·桑伯格。如果真的有“气候德性”这种东西,那她似乎就是模范人物——鉴于她做出的艰难的个人选择、她坚定不移的愿景以及她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给出解释并为他们的三心二意与不愿全身心投入而负责的勇气。如果这都不算践行了德性,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才是德性了——然而桑伯格身上也没有任何积极或乐观的地方。如果说有希望,那也是阴暗、冷峻的希望,饱含着对正在失去的事物的愤怒、悲伤与痛苦——但也充满着坚持、毅力和决心。毋庸置疑,即便一切努力终将白费,这位活动家至少也会继续抗争下去。没有乐观主义可言:非要说的话,那就是怀有希望的悲观主义,我相信它完全有权被称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德性。
怀有希望的悲观主义打破了老旧的乐观与悲观主义二分法。这一态度与视角在桑伯格与其他一些人物身上的体现,也在于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保罗·金斯诺思(Paul Kngsnorth)的问题:“是否有可能既看到未来的阴暗以及更趋阴暗、拒斥虚假希望以及自欺欺人的伪乐观主义,又不陷入绝望?”
需要避免的未必是悲观主义,而是无望、宿命论或放弃。对于绝望甚至也不必竭力去回避,因为它同样可以赋能并激励我们为变革而奋斗,但我们应当回避那种会导致人崩溃的绝望。这些都和悲观主义不是一回事,后者只是预设了一种阴暗的现实与未来观,但并不暗示你就要放弃勇气或者不必再坚持去争取更好的生活:相反,这些东西常常都是悲观主义的赠礼。
最渺茫的希望,最冷峻的安慰
一个人可以既怀有深刻而幽暗的悲观之心,被冰冷而坚硬的绝望包围,同时又不完全否定“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可能(它可以只是一种可能性)。这是一种珍贵非凡的希望,它绝非唾手可得,而是脱胎于一种痛苦的图景:承认生活里可能出现以及现实存在着的一切苦难。如果要问悲观主义者给了我什么教益,那就是:即便眼中为黑暗所充斥,这种古怪而散碎的开放性也仍旧是可期的,就像门上裂开了一条缝,令好事有机会进入生活。既然一切都是不确定的,那未来也一样,变坏和变好的可能性总是并存的。
以下所言本身就可以是一种道德立场:好事来了就欢迎它,并设法推动它沿既有路线继续前进,但也承认坏事而不试图把它解释掉(explain away)或者让意志在途中被压垮的人承受过多负担。有时我们并没有随心所欲改变世界的力量,承认这一点可能需要巨大的努力,也能带来莫大的安慰,与此同时又不至于磨灭促使我们为事业付出最优秀以及最艰苦劳动的那股驱动力。

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就曾在2006年的《激进希望》(Radical Hope)一书中写道,在文化毁灭的时期,一个常见现象就是旧价值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如果它们要在道德视界的崩塌之中存续下来,那就需要新的意义以及新的概念来重获生机。当中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与变革达成妥协,在旧德性依旧伴随着我们的情况下逐渐适应新的德性。我相信,这也是悲观主义服务我们的一种可能方式,不仅作为一种内在的德性,也作为一种赋予德性——它也是变革中的世界的一部分并随之而改变——以新意义的途径。以开放的眼光看待现实需要勇气,不要消极回避,要有耐心但不要轻易断定一切都完了:这就是希望。
希望——并非到头来一切都会变好,而是从来就没有什么东西会真正终结。这就是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曾经唱过的“万物皆有裂隙”(crack in everything),好坏皆然,因而这两者也从来不可能彻底远离我们。这并非坚信事情必然会变得更好——也不是粗放式乐观主义,它在一个崩坏的世界里不再成为德性,反而会成为困扰我们的恶习。打出“担保马到成功”的旗号,看似更有利于调动我们的积极性,但这种轻松具有欺骗性,因为它一碰上消极心态或宿命论就可能令人萎靡不振,且持续不断遭逢失望还可能会耗尽人的心力。
怀有希望的悲观主义则会要求我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为变革而奋斗,除了明白我们已经完成了变革时代呼唤道德行动者(moral agents)去做的那些事之外,便不再期待从我们的努力中得到更多的东西。这可能是——但它作为一种价值以及作为道德热情(moral fervour)的运用,也可能是未来最有利于我们的:一种因应脆弱时代的脆弱德性。
(作者Mara van der Lugtis系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哲学讲师,著有《贝尔、朱里厄与“历史与批判辞典”》与《阴暗事物:悲观主义与苦难问题》)
(翻译:林达)
来源:Aeo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