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有人认为女性天生愤怒,有人则指出女性需要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愤怒。对于女性在家庭生活、伴侣关系、朋友交际和工作场所中展现的愤怒,有不少书籍都提供了自助指南和批判分析,所以,丽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决定在她的《好不愤怒》(Good and Mad: The Revolutionary Power of Women's Anger)一书中写点别的。
丽贝卡·特雷斯特是一位新闻记者,始终以女性主义视角关注政治、媒体和文娱领域中的女性,曾遭遇过韦恩斯坦的谩骂。她说,“我珍视自己的愤怒,也珍视别人的愤怒,尤其是女性的愤怒。”《好不愤怒》不仅触及许多女性对于愤怒和沮丧的个人感受,更剖析了女性愤怒和美国政治之间的具体关系,审视这一情绪在政治话语里得到的回响,试图向我们呈现美国妇女的不满和憎恨如何引发了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运动。
人们对于女性的愤怒常常持诽谤或者排斥的态度,充满了偏见,正是这些偏见激起了女性的愤怒。这种对于国家的发展进步起到重要作用的愤怒,从来没有得到过赞美,甚至都很少被主流文化提及;女性的愤怒从来没有得到过赞扬,历史书里对于她们这种正义的愤怒往往只字不提。哲学家米夏·切莉(Myisha Cherry)尤其关注对于不公正现象的愤怒,这种愤怒“不是一种自私的情绪,一个对不公正感到愤怒的人并非只关心自己的境遇,而是对别人也很关心”,由此,许多个体的情绪汇聚起来,形成更巨大的愤怒,也走向更乐观的目标。

[美]丽贝卡·特雷斯特 著 成思 译
新星出版社 2022-5
特雷斯特最初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够借此疏导、理解自己的愤怒,“剖析自己是如何抑制愤怒,又是如何用更受官方欢迎的东西来遮掩愤怒的”,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在经历了2016年总统大选、特朗普上台之后,她转而以写作剖析美国女性的愤怒,审视这种愤怒遭到了怎样的压制、阻拦和贬损,目的只有一个:为愤怒正名。
《好不愤怒:女性愤怒的革命力量》(节选)
撰文 | [美]丽贝卡·特雷斯特 翻译 | 成思
在美国,从来不会有人告诉我们,不肯顺从、顽固执拗、狂烈暴怒的女性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的当下,引领了我们的行动,也推动了我们的艺术。我们应当了解这些。
其他文化里有着这样的故事。古希腊戏剧《利西翠妲》(Lysistrata)中,女性对自己的丈夫过于好战而感到生气,只有等他们停止战争才肯与他们性交。(从女性满足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特别两败俱伤的做法,但也的确彰显了女性的权力,让人们相信“如果女人不想让男人满足,就没有哪个男人能得逞”。)在另一个古希腊传说里,雅典名妓泰伊思为了报复一百五十年前波斯国王薛西斯入侵希腊时损毁雅典神庙,怂恿亚历山大纵火烧毁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polis)的神庙。在现实当中,饥饿而又愤怒的巴黎妇女因为面包价格的高昂而暴怒,她们在1789年10月向凡尔赛进发,这场凡尔赛妇女大游行后来助推了法国大革命爆发,最终推翻了路易十六的统治。2003年,在利比里亚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内战之后,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原住民和美裔利比里亚人在内的一群女性,因目睹战争造成的破坏而愤怒不已,齐声呼吁结束这场战争。在运动的开始,利比里亚和平活动家莱伊曼·古博韦(Leymah Gbowee)向众多愤怒的女性宣示:“从前我们保持沉默,但是遭受了杀戮和强奸、侮辱和疾病的肆虐之后……战争让我们明白了,要想拥有未来,就必须对暴力说NO,对和平说YES!”这场抗议活动持续了两年,直到2005年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当选利比里亚首位女总统,这场大规模女性运动才宣告结束。
尽管在美国没有这些故事流传,但女性的愤怒事实上也改变了美国。这些愤怒形形色色:对性别歧视的愤怒,对种族主义的愤怒,对恐同症的愤怒,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愤怒,还有对女性及周围人群遭受的许许多多不公正对待的愤怒。1991年一部讲述黑人女性活动家和艺术家的纪录片《愤怒之地》(A Place of Rage)里,有位女诗人琼·乔丹(June Jordan)“因为生错了性别,生错了时代,生错了肤色”而遭到自由的限制,她写下的诗作就是一部微妙的愤怒编年史。在片中,她回忆了让自己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变得敏感的事件:小时候她住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史岱文森区,邻居家的小伙子因为警察认错了人,在自家屋顶上遭到毒打,她目睹了这一切。“这个我崇拜的男孩,这个我们同街区的人……被这些充满暴力并且获准使用暴力的陌生人打得不成人形,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可怕了。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很早就在愤怒之地变得强硬起来。”

愤怒有力量
需要牢记的是,一直以来,人们对于女性的愤怒常常持诽谤或者排斥的态度,充满了偏见,正是这些偏见激起了女性的愤怒。黑人女性的愤怒和白人女性的暴怒会遭到区别对待;贫穷女性的懊恼和富有女性的愤怒也会得到不一样的倾听。然而,尽管美国以种种不公正的方式否定或者嘲笑女性的愤怒,这些愤怒往往还是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改变着这个国家的规则惯例和基本构造。
本书讲到了许多愤怒的女性。有些女性对于奴隶制和私刑深感愤怒,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名誉受损,为女性开拓公开表达意见的新形式,例如在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群面前公开演讲。有些女性因为妇女没有选举权而愤愤不平,从纽约市步行整整240公里到奥尔巴尼发起请愿,举行绝食抗议,甚至把自己锁在白宫的围栏上。有些女性燃烧了一辈子的怒火,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争取投票权,先是推动《第十九条修正案》的通过,再是促成《投票权法案》的颁布。她们在愤怒的驱使下发起一系列的非暴力反抗活动,她们游行示威,静坐抗议,非法投票,也为此遭到监禁和殴打。还有些女性将历史上那些隐秘的对话在露天集会和新闻报纸中传播散布,在法庭上、政治会议中和司法委员会面前讲述出来。
在美国,愤怒常常会起到推动作用,开启长期的法律和体制改革。事实上,在美国建国的经典叙事里,正是愤怒推动了美国人民发起革命,与英格兰决裂。然而,当愤怒的源头变成女性,当女性愤怒地要求自由、独立和平等时,不管她们再怎么煞费苦心地去模仿、去引用美国建国之父的那些语言表述和情感呼吁,她们的愤怒也很少会得到认可,很难被理解成是正义、爱国的愤怒。马萨诸塞州曾经有位名叫贝特,后来改名伊丽莎白·弗里曼(Elizabeth Freeman,又被尊称为“贝特妈妈”)的女奴,对主人平日里的虐待(甚至用滚烫的炊具击打她)愤恨不已,听到主人们谈论关于自由的革命言论后,她认为自由也应该适用于自己,进而提起诉讼争取自由;她的案例后来助推马萨诸塞州在1783年废除了奴隶制。本书剖析的正是这种愤怒的冲动。

19世纪30年代,洛厄尔纺纱厂的年轻女工们有感于自身的处境,发表了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相似的反叛言论,宣称“我们的父辈与英国政府的傲慢和贪婪浴血奋战,因而我们,身为他们的女儿,永远都不会戴上为我们准备的枷锁”。她们组织了罢工,成为后来愈演愈烈的美国工人运动的前身。七十年后的1909年,在库伯联盟学院(Cooper Union)召开的一场会议上,23岁的劳工组织者克拉拉·莱姆里奇(Clara Lemlich)听腻了男性发言人的长篇大论,拍案而起,呼吁发动一场大罢工。在此之前,她就已经因为参与罢工而遭到过毒打。这一次,她呼吁发起了两万人参与的制衣女工大罢工,与纽约绝大多数制衣厂达成了新劳工协议。三角内衣工厂是当时没有与工人达成新协议的几家工厂之一,这家工厂在两年后发生了火灾,146人丧生火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这场惨烈的火灾点燃了其他女性活动家的怒火,驱使着她们为改变美国工作场所的安全规定而努力。
愤怒的偏见
本书也意在指出,这种对于国家的发展进步起到重要作用的愤怒,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赞美,甚至都很少被主流文化提及;女性的愤怒从来没有得到过赞扬,历史书里对于她们这种正义的愤怒往往只字不提。有许多事情,历史书都没有告诉我们。例如,因拒绝为白人男子让座而遭到逮捕、从而引发1955年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的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是一位端庄娴静的女性,同时也是一名热诚的反强奸活动家。她曾经在一个企图强奸她的人面前宁死不屈。那时她10岁,面对白人男孩的威胁,她捡起一块砖头威吓对方不许靠近。“我当时非常生气,”她谈起年少的那次反抗时讲道,“他一声不吭地走了。”我们在学校的历史课上也学过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苏珊·布朗奈尔·安东尼(Susan Brownnell Anthony)等少数几位女英雄的事迹,却从来没人逼着我们去想一想,这些英雄事迹的动机不只是出于坚忍、悲伤或者毅力,其实更重要的是出于愤怒。而一直以来,我们所接收、所消化的文化讯息都在暗示我们,女性的愤怒是不可理喻的,是危险又可笑的。

本书还会指出,对女性来说无用的愤怒对男性却大有用处。例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竞选活动中大喊大叫,就会被称赞说他们能够理解那些支持者的愤怒,并且能够有力地引导这种愤怒。而他们的女性参选对手却只是遭到奚落,被嘲笑太过尖刻,只因为她们在麦克风前讲话太大声或者太过强势。本书论及的女性中,有些已经愤怒了太久,却一直没有找到发泄的出口,她们没有意识到在她们的邻居里,她们的同事里,她们的朋友、母亲和姐妹里,有多少女性和她们有着同样的感受。直到某一天,某位女性终于不顾形象地大声呐喊起来,于是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她的声音。因此,本书也会讲到女性的觉醒。例如,有些女性正是在女性大游行中举着标语前行的时候,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经历了某种觉醒,也开始思考自己之前到底是如何被骗,陷入沉睡的——而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此前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抗议活动。
这也就意味着,本书同时也会讲到女性内部针对彼此的愤怒:因某些女性——白人女性——熄灭或减弱自己的怒火换来特权和奖励而感到愤怒,也因其他女性——非白人,尤其是黑人女性——为此付出代价而感到愤怒,她们总有生气的理由,就算是压制自己的怒火也很少会得到赦免或奖赏。
愤怒于不公
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愤怒与宽恕》(Anger and Forgiveness)一书中指出,不管是个人生活中的愤怒还是政治背景下的愤怒,本质上都是一种报复性的冲动,这种惩罚性的冲动常常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然而,并非所有的政治愤怒都是出于报复性的冲动;愤怒并不一定是要看到总统和他的亲信被送进那些他们关押了无数美国人的监狱里去;愤怒也不只是来自那些想“把他关起来”的人们。愤怒也可以源于对不公正的强烈反感,源于想要解放那些被非法拘禁或伤害的人的渴望。对于女性而言,一直以来,她们的愤怒都遭到谴责、诽谤和嘲笑,被视为冒犯之举;一直以来,她们都在被迫压制愤怒、藏起怨恨,一旦选择表露自己的情绪,就会遭到阻拦——这才是报复性、惩罚性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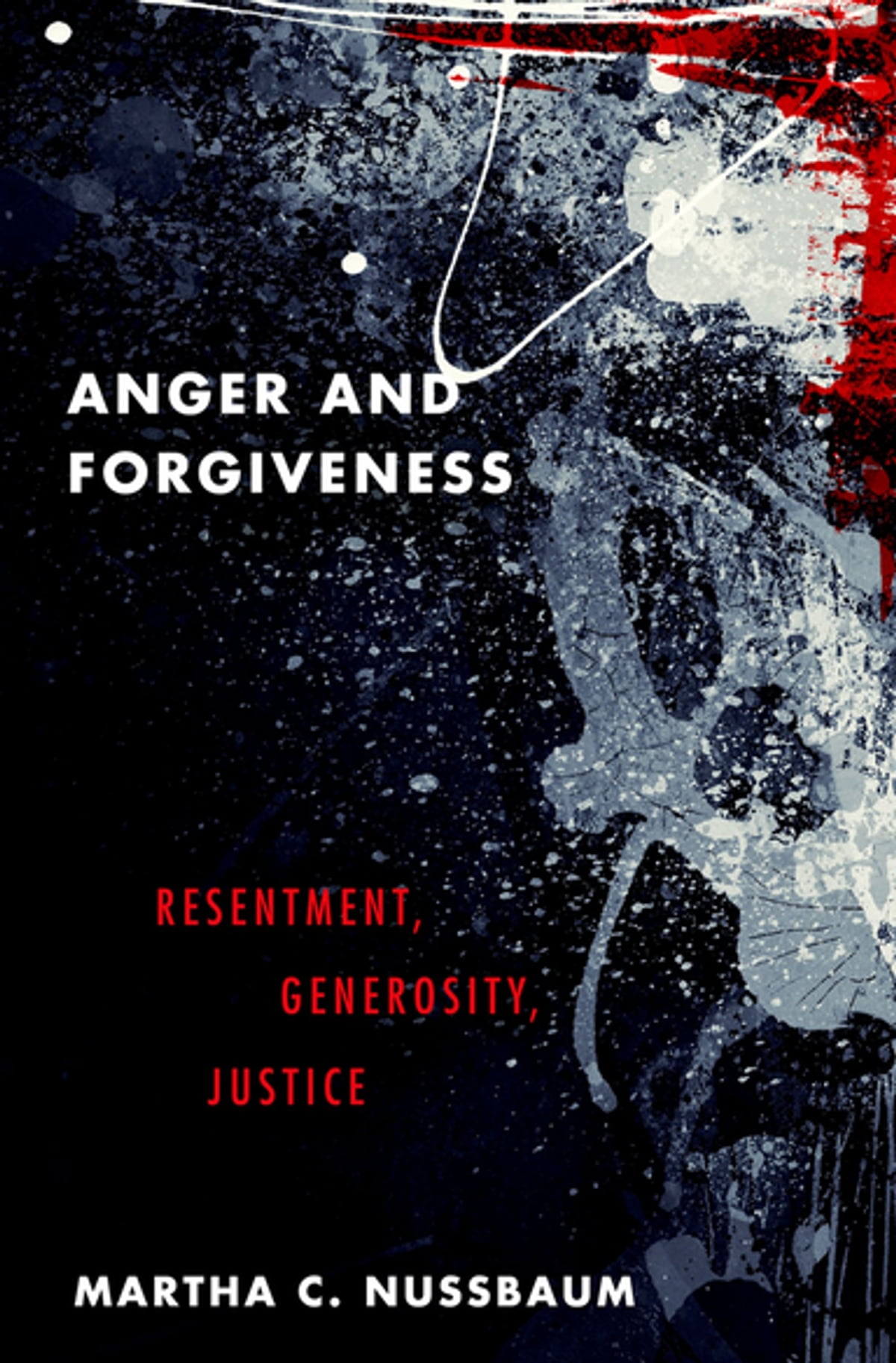
前不久,另一位哲学家米夏·切莉(Myisha Cherry)也指出:“我想让你们相信,有些愤怒并不是坏事。”对不公正现象的愤怒尤其让她感兴趣,她视之为一种针对不平等的恰当回应。“对不公正行为的愤怒有以下特点:它识别得出不法行为,并且基于事实,绝不是出于自己的妄想或编造;它不是一种自私的情绪,一个对不公正感到愤怒的人并非只关心自己的境遇,而是对别人也很关心……这种愤怒不会侵犯他人的权利,并且最重要的是,这种愤怒渴望带来改变。”
正如切莉指出的那样,政治的愤怒可以来源于个人的愤怒,也可以是一种个体的感受,但这种愤怒不同于努斯鲍姆笔下那种个体化的、惩罚性的愤怒,而是通常有更广阔、更乐观的目标。这种愤怒可以成为一种交流工具,号召有着同样思想观念的人行动起来、参与进来、合作起来。而这些人如果不首先将自己的愤怒公之于众,就永远无法知道原来自己拥有这么多足以集结一支军队的同胞,也无法超越各自的差异、展开强有力的合作。
本书希望指出女性愤怒中的温暖与正义所在,而不只是单纯地为之欢呼。愤怒毕竟有其局限和危险之处,也当然会遭到侵蚀。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愤怒就像是一种燃料,若加以必要的助燃剂,它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推动高尚而艰难的圣战。但它同时也易燃易爆,会爆发出无法预测的能量,会灼伤别人。
在这个愤怒卷土重来的时代,在这个女性被彻底气疯的时代,本书审视了愤怒这种情感在过去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带给了我们什么,又造成了什么伤害?与此同时,本书也发出了疑问:愤怒会将美国带向何方?从某种程度上讲,女性的愤怒从未得到过合理的对待,也从未得到过历史的认可,这着实让人生气。很少有历史学家或记者能够注意到,那些带着盛怒独自或合作抵抗暴政、抵制压迫、反抗不公的女性,推动了美国的发展与改革,也推动着这个国家一步步向前,实现其仍未兑现的人人平等的承诺。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多年来,人们一直对女性愤怒所具有的力量心照不宣:女性在美国是被压迫的大多数,在这个从来都得不到公平对待和公正代表的国家里,她们向来都有可能愤而起义、接管这个国家。也许,女性的愤怒之所以遭到如此广泛的诋毁,被贬为丑陋、敌对的无理取闹,正是因为我们深知女性的愤怒会带来爆炸性的威力,会翻转这个试图遏制这股力量的系统。回顾过去、着眼未来,我们会清晰地看到,那些权贵之所以通过消声、抹除和镇压来否定女性愤怒的举动,正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了女性愤怒的力量,一种能够改变世界的力量。
为愤怒正名
很多年来,我都在试图美化自己内心深处凝结的愤怒,让它变得可以为所有人接受。然而在允许自己发泄这些愤怒的时刻,我瞥见了愤怒的力量。我们谨慎克制自己的愤怒,但愤怒其实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愤怒是一种交流工具,能帮演说者和写作者释放表达,也能给那些有着各自烦恼的听众和读者带来慰藉。
我们当中那些感觉愤怒的人,那些煞费苦心隐藏愤怒的人,那些担心愤怒带来恶果的人,那些担忧发泄愤怒有碍于实现目标而牢牢压制怒火的人,都必须认识到愤怒常常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表达方式。愤怒是一种力量,为那些激烈而紧迫的战斗注入必要的能量、强度和紧迫感。更大而化之地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愤怒是正当合理的,它并不像别人告诉我们的那样丑陋可笑、歇斯底里或者微不足道。
起初,我决定写这本书,是希望能够借此疏导、理解自己的愤怒,剖析自己是如何抑制愤怒,又是如何用更受官方欢迎的东西来遮掩愤怒的,但是201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整整两年里,不管是政治媒体还是流行文化,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甚至于我的朋友每天都在告诉我,女性没有理由愤怒。他们告诉我,希拉里·克林顿的总统竞选之路不会遭到性别歧视的影响,事实上她才是拥有更多权力的候选人。他们告诉我,人们之所以支持唐纳德·特朗普,不是出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者仇外情绪,而只是因为经济焦虑。他们告诉我,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些特朗普支持者的愤怒,让这些美国白人陷入这种特朗普式狂热情绪的,正是那些女权主义者和民权活动分子的过激言论。我觉得自己也许会因为无法充分表达的愤怒而迷失方向。
于是我开始剖析美国女性的愤怒,审视这种愤怒遭到了怎样的压制、阻拦和贬损,虽然我十分确信这种愤怒在美国的成长与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我开始告诉别人,自己正在写作有关女性愤怒与社会变革的话题,也由此开始意识到,原来有那么多的女性是如此深切、如此绝望地想要谈论自己的愤怒。她们告诉我,她们需要阅读有关女性愤怒的讨论,需要书写自己的愤怒,需要谈论自己的愤怒,哪怕只是给我写一封邮件,或者给自己的朋友发推聊聊天。她们没有办法再继续抑制自己的愤怒,哪怕再多一秒。她们到底希望从这种愤怒的发泄中获得什么呢?我问过许多人。一次又一次,我得到的回答都是:为愤怒正名。

因此,我希望本书能够提供这样一种正名:那些愤怒的女性并不孤单,也不疯狂,更不会让人反感。事实上,女性的愤怒在美国历史悠久,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这历史被刻意隐藏了。
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些女性会突然开始愤怒,也会因这种突如其来的暴怒感到困惑,而她们并不是最先有这种感受的人,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女性表达过对于不公的愤怒。那些一直都在愤怒的女性已经做了很多,她们改变了美国的某些方面,也为女性树立了行动的楷模,提供了表达的范例。
我们必须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团迷雾之中,可能会迎来一个转折的时刻——不是说所有冤屈都会平反或者所有错误都会纠正,而是说这个国家的舵手有可能迎来巨变。美国的进步往往要让人备受煎熬地等上许久,但有时一些沉闷可怕、伤害极大的挫折却也在断断续续地推动进步的发生。我们如今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需要注意到、也需要认识到,如果我们认真想想自己因何愤怒,想想什么需要改变,就有可能带来怎样的改变。因为,改变是可以很快到来的。



评论